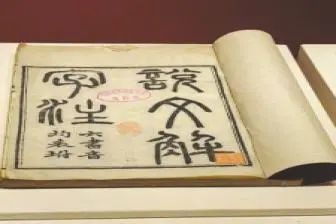在歷史展露出它尖利獠牙的時刻,原先生活中的小人物總是突然間發現自己掌握了從未有過的處置他人的權力,也把自己變成他人的獵物。
在“二戰”中,匈牙利王國爲了“恢復歷史領土”和納粹德國結盟作戰,還逐漸把農村的猶太居民有組織送往集中營,小鎮上的麪包師開始告發自己看不順眼的猶太顧客。到了1944年,德國扶持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黨”,取代準備和蘇聯媾和的霍爾蒂政權。在匈牙利知識分子哲爾吉·康拉德眼裏,“箭十字黨”分子都是些街頭混混和狂熱的、欲求無法發泄的年輕人。現在他們一躍成爲城市中的搜查者、處決執行者與暴力施行者。他們四處搜捕普通居民,把看不順眼的猶太人開槍打死扔進多瑙河,剩下的送往奧斯維辛。
經歷並記錄這一切的哲爾吉·康拉德,那時候還是個孩童。1933年出生在匈牙利農村的他,父母是當地成功的猶太商人,也是知識分子。在父母財富與人脈的幫助下,年幼的康拉德得以逃到布達佩斯,躲過了全村被送往奧斯維辛的命運。不過,在布達佩斯,庇護所的生活也可以說是九死一生:死亡像家常便飯,每天都有人消失,也有人意外地活着。一個女孩被抓到河邊槍斃,結果負責處決的機槍手發現自己打光了子彈,友善地笑了笑,把她放了。

大屠殺並不是一兩個瘋狂變態的殺人魔就可以犯下的罪行,但人們總希望有一兩個人足夠壞,壞到可以承擔所有壞事,這樣作爲普通人就可以開脫良心負擔。中東歐國家面對大屠殺時尤其如此。在波蘭,近年來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任何人如果公開表示歷史上波蘭人也是屠殺的幫兇,就會被視爲犯罪。而與國土在戰爭中被瓜分而留下了深刻創傷的波蘭有所不同的是——許多匈牙利人一開始就熱忱地投入到戰爭中來,但戰爭結束後又急切地爲自己尋找受害者身份。
這種想開脫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畢竟和納粹德國並肩作戰的霍爾蒂政府只是個威權保守政府而非法西斯政權。如果“箭十字黨”在戰爭一開始就上臺,那麼匈牙利猶太人就不會最後還剩下25%,而是會像波蘭猶太人那樣,被“徹底解決”了。但儘管霍爾蒂的統治有不少自主權,他還是在“箭十字黨”上臺前就把康拉德的同村猶太人全部送去了奧斯維辛。在村子裏活下來的只剩康拉德一家——他的父母被抓走後,運用手段把自己送去了奧地利,躲開了奧斯維辛和比克瑙的滅絕營。
“所幸”有“箭十字黨”存在,他們夠壞。相比冷漠的威權政府,“箭十字黨”是狂熱的真納粹,是他們讓德國軍隊“佔領”了匈牙利,欺壓匈牙利人。霍爾蒂的匈牙利政府成員,也下野的下野,有人被關押,有人被殺死,也成爲了“箭十字黨”的“受害者”。1944年,遂成爲匈牙利喪權辱國的標誌性時刻。
2014年,時隔70年,匈牙利政府在布達佩斯市中心正對着蘇軍解放紀念碑的廣場上興建了一座雕塑,以提醒人們記住1944年德國佔領匈牙利的黑暗歷史。這尊新紀念碑下方是手持天主教洛林十字的一位天使,象徵着匈牙利王國;天使頭頂是一隻腳上刻着“1944”的黑鷹,惡狠狠地撲將下來,象徵着德國納粹。巨鷹撲食,天使惶恐柔弱而無助,可誰會記起這天使也曾經是黑鷹的同僚?
長達40餘年的冷戰時代,則爲匈牙利人提供了另一套面對歷史的勇氣。新政權重新勾勒了階級史觀——1950年代開始的官方敘事認爲,“二戰”中匈牙利的統治階級和德國納粹政權沆瀣一氣。這幫助無產階級和普羅大衆在戰爭歷史面前恢復了平常心。儘管在康拉德這樣經歷了戰爭和屠殺的人的記憶中,平民和精英在暴行中只是位置不同,到頭來是各自以各自的方式推動了那些不堪回想的歷史進程。
在布達佩斯市中心,近些年重新裝修、布展開放的恐怖之家(house of terror)展示着後冷戰時代歷史記憶的整套機制:外牆天頂和正門入口處,巨大的“箭十字”和五角星標誌並列在一起,一邊黑色,一邊紅色,以象徵匈牙利同時是納粹和蘇聯的受害者——這套受害者敘事,是當代匈牙利理解20世紀曆史的基本方式。

在這座曾經用作蓋世太保和“箭十字黨”祕密警察總部的建築裏,1950年前後入駐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祕密警察——同樣的建築,同樣的國家機器,甚至部分人員也可能是相同的。走進鋼筋混凝土製昏暗潮溼陰冷的地下室,曾經的監牢裏陳列着被“箭十字黨”和人民共和國政權處決的匈牙利舊精英的照片。受害者的眼睛和參觀者的眼睛在這裏穿越時空對視。然而諷刺的是,這些今天匈牙利人憑弔的舊精英,曾經無法拒絕“生存空間”的誘惑,發動匈牙利軍隊遠征烏克蘭草原攻擊蘇聯紅軍;也默許在自己眼皮下,一車皮一車皮的匈牙利猶太人送到奧斯維辛,灰飛煙滅。
以紀念的方式和過去的歷史匆匆和解,再補上對“極權主義”的仇恨。這樣的場面,在中歐、東歐的許多國家算是常態,和人們印象中德國總理下跪道歉的戰爭清算,形成另一種對比。曾經是第三帝國一部分的奧地利,戰後獲得獨立,並且利用自己在冷戰最前沿的身份,得到了一個“最早的納粹受害者”的身份,不用再面對“奧地利爲什麼在‘二戰’前選擇和納粹德國合併”的問題;如今執政聯盟的一部分——奧地利自由黨,則在歷史上和納粹舊官僚曖昧不清,至今爲人詬病;波蘭也閉口不提,“二戰”前參與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和國內的反猶情緒……
無法迴避的是,“二戰”前的那個歐洲——尤其是中歐和東歐,遠比今天這片土地多元、甚至更包容。在那個時代的維也納、布達佩斯,族羣混合已經是家常便飯。而到“二戰”結束時,人們驚訝地發現,由死亡、廢墟和毀滅所創造的這個戰後新歐洲,某種程度上的確更符合納粹的想象——歐洲的許多國家變成了更純粹的民族國家,許多大都市變成了單一民族的都市。在波蘭、匈牙利、奧地利和德國,原先佔人口比例數分之一的少數族裔消失了。戰後秩序帶來的國界重新劃分,把周邊一系列匈牙利人佔據關鍵少數族羣身份的土地繼續劃給了周邊國家,創造了一個更加“純化”的匈牙利(匈牙利民族主義者對失去這些土地憤懣不平,儘管他們加入“二戰”的納粹一方就是想通過戰爭“拿回”這些地方)。
作爲見證了戰前歐洲的人,康拉德活過了戰爭,面對着一個陌生的“新歐洲”。他成爲一個母語是匈牙利語、卻失去了絕大多數自己社羣成員的匈牙利猶太人。環境讓他養成了一種特質:放棄尋找故鄉。“我到一個新城市的第一天——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大還小——我都能想象自己在此度過餘生。”不過,當所剩不多的猶太裔選擇移居以色列的時候,號稱可以隨遇而安的他選擇了做一個匈牙利公民,當1970年代稍見寬容的總書記卡達爾治下,政府試着讓他出國生活的時候,他選擇了留下。
康拉德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匈牙利猶太知識分子。他還證明,就算在不那麼能夠隨心所欲的情況下,仍然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值得做並且也需要有人來做。他和朋友出遊,做社會調查,做社工家訪,觀察人間百態,並把這些觀察寫成文章和小說,他甚至還在精神病院做護工,或應徵殯儀館的工作。隨着戰後匈牙利施行的斯大林模式——清洗與緊急狀態的終結,生活變得不再嚇人,但也沉悶而無聊——隨時出現的用來抓人的黑色大轎車,變成了日復一日去單位上班的乏味日常,至多是攢錢到十年後去南斯拉夫克羅地亞海邊旅遊。“土豆燒牛肉”,赫魯曉夫出訪布達佩斯時格外欣喜,更遠的地方則有人寫詩嘲諷。這種平庸的日常,其實就像“歷史的終結”提前降臨一樣。東歐最終的鉅變並不是因爲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而是這種生活受到了經濟狀況的侵蝕而難以爲繼。

康拉德筆下的自己,出奇冷靜也出奇沒有強烈的政治情感。1956年布達佩斯的暴動中,康拉德幾乎抽身事外。他的頂頭上司熱心投入起義,但他自己拎着機關槍,選擇了到處溜達。他有沒有用文字隱藏自己那時的任何狂熱舉動,以使自己和今天的匈牙利民族主義政治劃清界限?我們不得而知。但一個已經覺得自己是異鄉人的人,也許確實很難投入其中,何況那場事件涵蓋了太複雜的政治光譜。“那次暴動中,有很多人是原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聊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認識的俄羅斯反普京左派憤憤不平地說。作家其實一直都不合時宜,也不像俄國書寫者那樣充滿戲劇展演。異議身份更像是當權者給他的加冕,而非不斷犧牲、不斷鬥爭的想象中的堅毅人格。
恰恰是1990年後東歐轉型,作家開始和時代產生距離。康拉德的朋友塞勒尼把整個私有化過程稱爲“無須資本家打造的”資本主義,用冷靜的筆調揭示曾經的許多異議知識分子如何在新體制下成爲最得益的羣體之一。這樣的知識分子位置,並不是經歷了大大小小事件的一代人能夠輕易適應的。他們失去了對手,轉型爲了既存事實的辯護者,光環僅限於過去的,被戴上標籤的知識分子,失去了模糊的異鄉人身份。新的身份把他們推上危險的,毫不適應的戰場。
後轉型時代的匈牙利,先是嘗試穩固兩黨制,卻又在一種自保的心態中愈發遠離了有活力的政治。中右翼維克多·歐爾班基本確立了民族主義、保守主義與排外新右翼合流的一黨獨大路線。而對這樣的變化,康拉德的反應停留在了1980年代。
2018年初,在一次訪談中,康拉德猛烈抨擊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他建議歐爾班放棄權力,以免變成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下場。這些話激怒了歐爾班及帶有威權傾向的匈牙利執政黨。他們認定,康拉德在傳遞煽動和暴力的語言。“康拉德說要殺死歐爾班,就像羅馬尼亞人殺死齊奧塞斯庫一樣”,親歐爾班的媒體集中火力。
這一切,源於歐爾班政府對金融大亨索羅斯的攻訐。他的政府着力打擊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將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理念描繪爲國際銀行家削弱匈牙利主權的陰謀。索羅斯是另一個逃過浩劫的布達佩斯猶太人,但他的軌跡和康拉德截然不同——更富爭議、更沒有祖國,作爲資本的化身,隱身在陰影中,更像納粹所描繪的陰暗的國際金融資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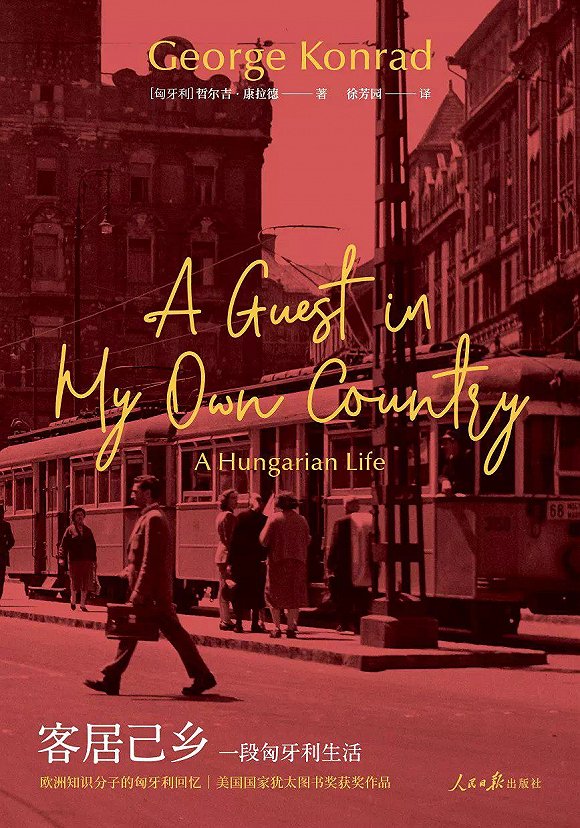
《客居己鄉》 [匈]哲爾吉·康拉德 著 徐芳園 譯 三輝圖書·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9年1月
無奈又或是諷刺的是,在這件事情上,兩個人生軌跡並不相同的人共同代表了同樣一種觀念——“反自由”的歐爾班政權的對立面。這種綁定是否有問題?無論如何,今天的布達佩斯,像是因爲20世紀的記憶太過沉重,而儘量選擇了遺忘。今天的布達佩斯,就和東歐的許多城市一樣,分爲舊城新城旅遊區和居民區,散落着飾品店食品店遊客商店和餐館。相比這些,它揹負的歷史太沉重了。
這倒是讓今天的世界,反而顯得比昨日更遙遠,更難以捉摸了。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