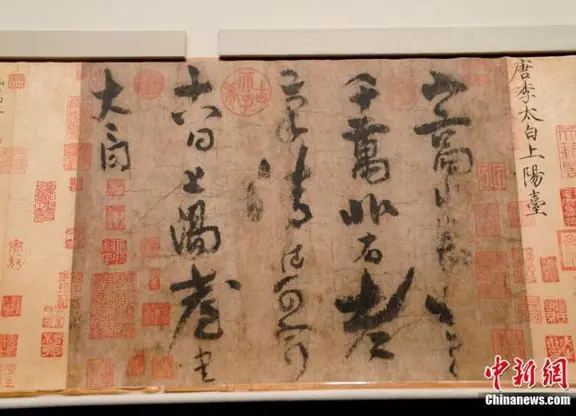如果說關於遠程工作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很多人喜歡遠程工作,不希望老闆取消它。
當疫情迫使辦公室員工進入封鎖狀態,並切斷他們與同事面對面交流時,他們立即意識到,他們更喜歡遠程工作,而不是傳統的辦公室日常和規範。
隨着一些辦公室和學校重新開放,各個年齡段的遠程工作者都在考慮自己的未來,許多美國人正在發出尖銳的靈魂拷問:他們是否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以及他們願意在未來幾年犧牲或忍受什麼。
甚至在疫情爆發之前,就有人質疑辦公室生活是否與他們的抱負相符。我們花了數年時間研究“數字遊民”,即那些離開了家園、城市和大部分個人財產,開始他們所謂“旅居”生活的員工。這項研究告訴我們,是什麼樣的處境迫使員工遠離辦公室和主要的大都市地區,並將他們推向新的生活方式。
如今,很多人都有機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塑自己與工作之間的關係。
大城市的誘餌和交換
大多數數字遊民一開始都很興奮地進入爲知名僱主工作的職業發展軌道。搬到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城市後,他們想利用空閒時間去結識新朋友、參觀博物館和嘗試新餐廳。而後,倦怠襲來。
儘管這些城市肯定擁有能夠激發創造力和培養新關係的機構,但數字遊民很少有時間利用它們。相反,高昂的生活成本、時間的限制和工作上的要求導致了一種壓抑的物質主義和工作狂文化。

高昂的生活成本、時間的限制和工作上的要求導致了一種壓抑的物質主義和工作狂文化。圖片來源:Alex Kotliarskyi/Unsplash
28歲的寶琳在廣告業工作,幫助大公司客戶用音樂建立品牌形象。她將同齡專業人士的城市生活比作“倉鼠轉輪”。(按照研究協議的要求,本文使用的名字爲化名。)
“紐約的特點是,它有點像最忙之人的戰鬥,”她說,“這就像,‘噢,你以爲你很忙?不,我才叫很忙。’”
在我們的研究中,大多數數字遊民都曾被吸引到城市規劃專家理查德·弗羅裏達稱之爲“創意階層”的工作中——即設計、技術、營銷和娛樂方面的工作。他們原以爲這項工作會是充實的,足以彌補他們在社交和創造性追求上所犧牲的時間。
然而,這些數字遊民告訴我們,他們以前的工作遠沒有他們期待的那麼有趣、有創意。更糟糕的是,僱主繼續要求他們“全身心投入”工作,並接受辦公室生活的種種控制,卻沒有按照承諾給他們提供指導、發展或有意義的工作。當他們展望未來時,他們看到的只是更多相同的前景。
33歲的埃莉曾是一名商業記者,現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企業家。她告訴我們:“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沒有積極的榜樣,所以人們就會想,‘爲什麼我要不斷往上爬,努力得到這份工作?這樣度過接下來的二十年可不像個好辦法。’”
在年近30歲到30歲出頭的時候,數字遊民們在積極研究如何離開他們在全球一線城市的職業軌道。
尋找新的開始
儘管他們離開了世界上那些最迷人的城市,但我們研究的數字遊民並不是在荒野中工作的自耕農。他們需要獲得當代生活的便利,纔能有生產力。放眼海外,他們很快了解到,印尼的巴厘島和泰國的清邁等地擁有必要的基礎設施來支持他們,而成本只是他們以前生活成本的一小部分。
隨着越來越多的公司爲員工提供遠程工作的選擇,我們沒有理由認爲數字遊民必須前往東南亞,或至少離開美國,才能改變他們的工作與生活。

新的自由和新的機遇在等着你 圖片:Getty Images
疫情期間,一些人已經離開美國國內房價最貴的大城市,搬到了小一些的城市和城鎮,以便更親近自然或家庭。其中許多地方仍然擁有充滿活力的當地文化。隨着上下班通勤從日常生活中消失,這類搬遷可能會讓遠程工作者有着更多可用收入和更多空閒時間。
在我們這項研究中,數字遊民經常利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和金錢來嘗試新事物,比如探索副業。最近的一項研究甚至發現,(有點看似矛盾的是)從事副業帶來的賦權感實際上提升了員工在主要工作中的表現。
未來的工作雖然不會都是遠程的,但無疑會爲更多人提供更多的遠程選擇。儘管一些商界領袖仍然不願接受員工想要離開辦公室的願望,但地方政府正在擁抱這一趨勢,美國的幾個城市和州——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國家——都在制定計劃,以吸引遠程工作者。
這種移民,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有可能豐富社區,培養更令人滿意的工作和生活。
(翻譯:劉溜)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