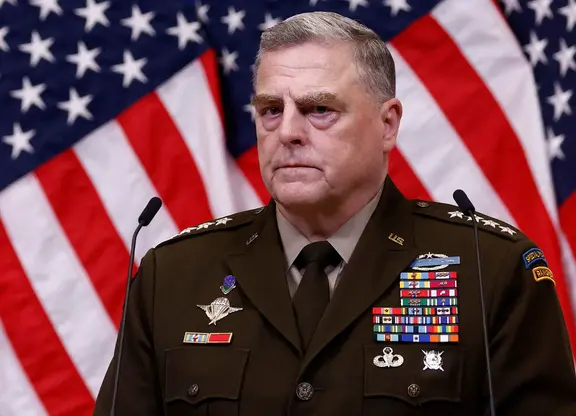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11日宣佈美國將對參與調查美在阿富汗戰爭中行爲的國際刑事法院(以下簡稱ICC)官員實施經濟制裁和入境限制,原因是美方認爲ICC的調查行爲涉嫌違規。據悉,美國的制裁決定受到了包括歐盟在內的多國政要和相關非政府組織的譴責。
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已經多次向有關國際組織實施制裁或者施加威脅。早在2017年,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妮基•黑莉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就表示美國正“仔細審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及美國在其中的角色,而美國將在考察“他們是否真的嚴肅對待人權”後決定本國是否繼續留在理事會內。隨後,制裁的矛頭又轉向了世貿組織。2018年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如果世界貿易組織再不改進的話,美國將退出。”同年10月,美國又宣佈啓動退出萬國郵政聯盟程序。而就在今年的6月,特朗普在美國新冠病毒疫情白熱化的時刻又宣佈了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的決定。
選情告急 特朗普“向外”謀求“自救”
可以說,特朗普上任以來就開啓了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的“退羣”行動,而近年來這一行爲愈演愈烈並不斷挑戰世人的認知,尤其是美國此次制裁ICC官員更是“跌破底線”。究其深層原因,無疑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將近。
總統大選對於美國政治而言是一個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時間節點。對於共和黨與民主黨這樣的“選舉型政黨”來說,總統大選無疑都是本黨的“一號議程”。然而,今年的選舉是在新冠疫情和反種族歧視運動衝擊特朗普政府公信力這一極端特殊的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間表現出的低效率和反覆無常不禁讓人們懷疑特朗普政府的執政能力;另一方面,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則直接引爆了積蓄在美國社會中的不滿情緒,其迸發出的怒火直接延燒到了白宮。毫無疑問,反種族歧視運動引發的大規模社會騷亂以及特朗普本人對這次騷亂的多次堪稱“火上澆油”的表態,更是給他的連任蒙上一層陰影。根據今年6月8日發佈的CNN民調結果顯示,特朗普比前副總統拜登落後了約14個百分點,支持率分別爲41%和55%;同時CNN還指出,特朗普總統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已跌至自2019年1月以來的最低谷。原本躊躇滿志的特朗普卻遭遇了選情“反轉”,因而不得不另想辦法“自救”。在內政乏善可陳的情況下,如何尋找並攻擊國際“標靶”成了其轉移矛盾與挽救選情的不二之選。
制裁ICC官員 特朗普繼續向外轉移矛盾
此次ICC在美國大選將近的節骨眼上,宣佈就美軍在阿富汗衝突期間可能發生的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進行調查,無疑讓剛宣佈退出世衛組織的特朗普再次面對來自國際的壓力。首先,這一調查即便沒有最終的結果,其過程本身就意味着對美國形象的重大打擊。其次更爲重要的是,在總統大選逐漸白熱化之時,任何有關特朗普政府的負面新聞都會被民主黨人牢牢抓住並大肆攻擊,這顯然也是特朗普政府不願意面對的局面。因此,多方因素疊加並基於此前特朗普政府多次“甩鍋”的慣性,宣佈制裁ICC的相關官員就變得不那麼令人迷惑了——它不過是另一個升級版的“甩鍋”行爲。
通過制裁ICC的相關官員,特朗普政府藉機向國內民衆展示美國強硬的國家態度和強大的國家能力,試圖喚起民衆對政府的信心與民族情感。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道,就在美國宣佈制裁ICC相關官員的當天,美國白宮發言人凱莉•麥肯內妮就發表聲明稱ICC的調查是一個“有政治動機的策略”,其目的是傷害美國。同樣在當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司法部長巴爾還指責俄羅斯“操縱”ICC,但卻未提供相關證據,而這無疑也是出於通過樹立“外敵”轉移國內矛盾的考慮。
國際舞臺“四處點火”不利於美國利益
然而從長遠來看,對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的抵制與威脅並不符合美國利益。事實上,大部分戰後的國際組織是美國憑藉自身強大的綜合國力和超然的國際地位而主導建立的,長期以來都是維持霸權和話語權的重要載體。而一些非西方發展中國家針對國際組織“提升包容性”的改革呼籲與方案也並沒有也無意“另起爐竈”。但特朗普政府卻把這些要求視爲“修正主義”,其抵制、退出甚至制裁國際組織的霸道行徑與美國曆屆政府對多變國際機制工具主義的態度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升級,也將進一步使美國在國際上喪失道義與話語霸權,從長期來看還會激發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國家的不滿,盟友們的“貌合神離”也將愈發常見。就在6月14日,歐盟外交事務高級代表博雷爾宣稱歐盟並不會在中美緊張的關係下“選邊站”,相反歐盟會“走自己的路”同時與北京和華盛頓爲共同利益而合作。
從相對意義上來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對維護國際秩序負有重要責任。而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動輒宣佈“退羣”並對相關國際組織進行威脅或宣佈制裁是一種極其不負責任的表現,不僅“打了自己的臉”,而且從根本上不利於國際秩序的穩定。
(來源:中國網)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