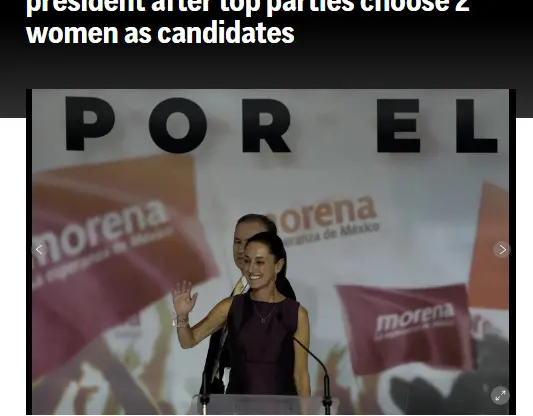在親眼看見了2022年奧斯卡頒獎禮上那一記“讓全世界都聽見了的耳光”後,如我(指本文作者H. Colleen Sinclair)所料,網民一下子分成了兩派:威爾派和克里斯派。
作爲一個研究攻擊性(aggression)的社會心理學家,我也能預見到爲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s)拿他妻子的禿頭開玩笑,被他打了一耳光——辯護的觀點大都類似於:這名演員只不過爲保護妻子“做了有必要做的事”,並且這樣做才讓他像個“真男人”。
這些辯護含有社會科學家所稱的“榮譽文化”(culture of honor)的元素,它在世界上的一些特定地區、族羣以及亞文化裏佔據着主導地位。
榮譽文化是如何興起的
榮譽文化要求,男性在面臨侮辱或威脅時,應以充滿攻擊性的方式捍衛自己的聲譽,且這一命令還延伸到了保護妻兒及財產等事務上。受到輕慢而不強勢反擊,則會被認爲不像個男人。
這一概念可能容易與“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相混淆,後者標誌着反女性主義的、過度的男子氣概,推崇獨立、情感上的遲鈍以及攻擊性,以確立男子對女子的統治地位。事實上,新近的研究發現,這兩個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榮譽文化更多關乎對女性的仁慈以及騎士精神。然而,這兩個概念也可能會產生重疊,在相對傳統的文化裏尤其如此。
研究者主張,榮譽文化在那些執法不嚴或者無法可依的社羣裏更容易興盛起來,例如19世紀的美國西部以及非洲與拉丁美洲的遊牧人羣體。這一研究成果還有助於理解一些對警察信任較低的市中心社羣何以暴力頻發。
在這些地區,男性的聲譽成了他的第一道防線。如果人人都知道冒犯他或者他的家庭必然會受到懲罰,那抱有冒犯企圖的人就不太容易去鋌而走險。
當一些人認爲暴力是可接受的
針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可追溯到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奈斯比(Richard Nisbett)和道夫·科恩(Dov Cohen),二人試圖解釋爲何美國南部及西部的兇殺案發生率比全美其它地區要高出許多。
在對比犯罪數據後,奈斯比指出,兇殺案發生率的差異之成因,在於西部與南部的高兇殺率關涉到論證(arguments)。問卷調查顯示,美國各地區對暴力的容忍度普遍都不算高。但來自南方的答題者更傾向於認爲,若一個男人或他的家庭受到了羞辱,那暴力就可以得到辯護。
在後續的研究裏,科恩和奈斯比還隨機向全美各地的企業發送了兩份求職申請當中的一份。每份申請均附有一封求職信,申請者在其中解釋了自己的重罪前科,將之歸結到年輕氣盛之類的問題上。在一半的求職信裏,重罪的名目是偷盜汽車,另一半則是受辱後憤而殺人。研究者發現,若僱主來自榮譽文化盛行的州,那麼這位虛構的兇手就能收到比偷車賊更多的答覆——且語氣上也表示了更多的理解。
在同一研究中,科恩和奈斯比面向全美招募了一批大學生記者,並隨機安排他們寫一篇故事,故事內容在關於羞辱的殺人與關於重罪的殺人之間二選一。研究者發現,負責撰文的記者出身的州如果榮譽文化盛行——如德克薩斯、亞拉巴馬和蒙大拿——他便會用更加正面的口吻來形容受辱殺人者。
在其它一些實驗裏,研究者還表明,一個信奉榮譽意識形態的人在受辱後會有更高的睾酮以及皮質醇水平,這兩種激素都與進攻性及壓力有關。他們原諒冒犯者的意願更弱,在受到輕慢之後更難讓自己恢復冷靜。最後,他們在問卷裏回憶最近受到的一次侮辱時,也表現出了更大的憤怒以及更強的恥感。
毫無悔意
在現實世界裏,與榮譽信念體系更加親和的地區更可能發生校園槍擊案。在同一批州里,被定了罪的兇手在臨刑前也更少表現出悔恨。不過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針對諸如校園槍擊案及死刑這類統計上較爲罕見的事件下定判決性結論時也是要萬分謹慎的。
在威爾·史密斯以“理查王”這一角色獲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之際,他讚賞了理查德·威廉斯爲捍衛自己家庭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做法。在許多觀察家看來,史密斯這是企圖援引榮譽與騎士精神之類的德性來辯護自己先前打人耳光的行爲。
當然,文化差異不是影響人們被打耳光後有何反應的唯一因素。例如,你也可以預期到喜劇演員們會出於團結而支援克里斯·洛克,種族主義的反應也必然會出現。
話說回來,在這麼多人急於宣佈“暴力絕不是答案”的當下,對其他一些人來講,暴力事實上可以是答案——其成因至少部分地在於,榮譽文化還是一如既往地興旺。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