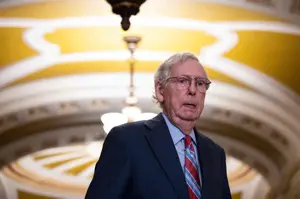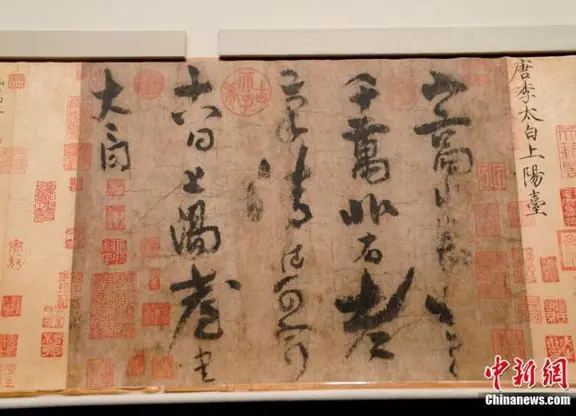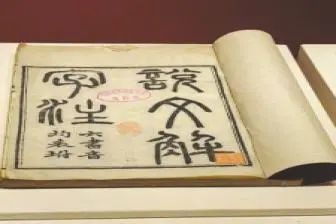2019年完結的劇集《德雷爾一家》改編自英國自然作家傑拉爾德·德雷爾的《希臘三部曲》,講的是喪偶的母親帶着四個孩子離開陰冷的英國伯恩茅斯,來到希臘小島科孚居住的經歷,這裏“每天都有那種安詳靜謐、光陰止步的感覺”。今年開播的英劇《萬物既偉大又渺小》則改編自同名小說,講述了年輕獸醫吉米·哈利在鄉間行醫生活的經歷,觀衆在其中得見北英格蘭約克郡鄉間人與動物百態。
這兩部作品有一些共通之處,比如都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故事都發生在一戰結束後、二戰開始前的歐洲,並且主人公都在戰爭陰影之下和現實生活的痛苦之外,營造了一片世外桃源。在今天,觀衆即便沒有注意這些故事的時間和背景設定,也一樣能夠在當中得到治癒。
這種治癒來自於賞心悅目的自然環境——德雷爾一家俯瞰大海,周圍是樹林與果園,吉米·哈利目之所及都是無盡的碧綠草地。在這裏,人與動物相處就像親人朋友,人對所處的自然保持尊重和剋制,人與人之間則相互依存、彼此關照。這些要素讓現代都市的人們對某些缺失之物心生渴望,滋長出了某種濃烈的懷舊與思鄉之情。
人與動物
在《德雷爾一家》當中,一家人對待動物的方式是和它們生活在一起,人們給予動物食物和照顧,並允許它們在家裏走來走去、飛來飛去,沒有過多收養,也沒有讓它們擠在籠子裏。在真實生活當中,傑拉爾德一生與動物爲伍,花了大半輩子時間經營動物園,不過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地球不再有瀕臨絕種的動物,也不再有動物園存在的必要。傑拉爾德到20世紀50年代已經收養了相當數量的小動物,他並沒有賺取“展覽費”而捕獲表演物種。在當時的人們眼中,放棄這筆可觀的收入是愚蠢的,不過,他即使陷於窮困也未曾動搖。

《德雷爾一家》第四季 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在《萬物既偉大又渺小》裏,從事獸醫工作的吉米·哈利主要與鄉村裏的豬牛馬羊打交道,也會關照村民養的寵物貓狗。在第一集裏,他被馬踢倒,弄得一身髒泥;被體形龐大的公牛嚇得站到了牆上;他給難產的母牛接生,把手伸進產道,費盡全身力氣把小牛拉出來……這些工作固然辛苦,但他所面對的鄉間動物是真正悠然生活在田野的。很多時候,動物們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大公牛“克萊夫”和母牛“冰糖”,它們需要勞作卻並非苦力,而更像農民的朋友、親人或兒女。
獸醫西格弗裏德·法農和哈利在鄉間有過這樣的對話。法農給哈利介紹短角牛,他說,這種牛如今都要滅絕了,因爲荷蘭牛的產奶量要大得多。哈利回答說:“如果一個農民花同樣的時間能夠得到更多的奶,那我覺得是好事。”法農反問道:“但代價是什麼呢?這個地方有自己獨特的氣息,短角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們一旦消失,這個山谷就會又失去一點獨特性。”
如今還有多少山谷擁有自己的獨特性,鄉間的動物又有多少仍自在生活?有多少人會像傑拉爾德一樣,哪怕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也不讓動物處在擁擠的環境中,不讓它們去展覽、表演賺錢呢?現實生活中,很多動物已經不復自在自爲,動物成爲人牟利的工具,動物和人的關係變成了奴役和虐待的關係。

《萬物既偉大又渺小》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人和動物的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飼養動物在戶外放養,吃的是蔬菜和種子,活蹦亂跳,如今工業化養殖之下,動物被集約化監禁飼養,飼養空間十分狹窄。倫理學家、《動物解放》一書作者彼得·辛格看到,動物的五項基本自由(轉身、梳毛、站立、臥倒、伸腿)在這種情況下難以得到保障。雞吃的是高能量食物,在籠子裏幾乎動彈不得;奶牛生活在不長草的牧場裏;牛犢短暫的一生都在吃液體飼料,在75釐米寬的格欄裏難以伸展四肢……這些動物不再擁有自己的名字,變成了養殖場的一個個數字。
人與自然
與《德雷爾一家》《萬物既偉大又渺小》所展示的田園牧歌不同,現實中的人們一直心存把動物、土地轉化爲金錢的渴望。就在吉米·哈利開始在英格蘭鄉村當獸醫的30年代,也正是德雷爾一家在希臘科孚的30年代,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狂飆突進的美國西部大開發中,在利潤的刺激之下,人們不計後果地翻耕大平原,剝光了那裏千百年來固定土壤、抵禦風蝕的植被。《骯髒的三十年代:沙塵暴中的美國人》講述了大規模的土壤侵蝕和塵暴的到來,讓人們生活的世界如同漫漫長夜,人們因爲塵肺疾病而死去。那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環境危機之一。
上個世紀60年代,人們開始反思征服自然的意識形態。美國曆史學家、環境史學的創始人之一唐納德·沃斯特在《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裏看到,問題的根源而在於一種文化——這些環境問題是由資本主義的精神引發的,拜金主義取代了人與土地的依存關係,對無限財富的追求取代了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農業生態失敗和人們持有的價值觀、對成功的看法和獲得成功的方式密切相關。在廣告宣傳和物慾刺激之下,人的慾望被放大到遠遠超過自己的需求,鄉村的人們緊盯城市社會的生活標準,“人們沒有按照社區自身的節奏來生活,而是盯着遠方的陀螺,這樣的生活態度也成爲了他們採取的高度商業化農業的重要部分。”

《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25週年紀念版)》 [美]唐納德·沃斯特 著侯文蕙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7-1
在城市裏,慾望的放大讓人們變得越來越忙碌。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朱麗葉·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一書中提出了“工作-消費循環”,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裏也有過類似的論述。人們用物質消費的刺激取代空閒時間來消解自己的慾望,這樣無異於飲鴆止渴,不僅不能持久,還會推動慾望不斷升級,人們爲此再增加勞動時間,進一步削減空閒。而沒有進入工作-消費陷阱的人,不是不會落入,而是無力落入。如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的,被排除在消費之外的“新窮人”由於沒有購買力,在物質與精神上都被拋棄。
在大城市,以消費爲實現自我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爲大衆化現象,攀比消費成爲了過度勞動的重要誘因,人們爲了永不饜足的消費慾望拼命加班、超負荷兼職、頻繁跳槽……在農村,唯一的辦法就是向自然索取,利用土地既不取決於土地本身的要求,也不取決於當地人自身產生的需求,而取決於來自於商人的無情的壓力。沃斯特看到,一種對消費至上的無個性的認同樹立起來——“錢,更多的錢,是參與那個世界所必須的。”
爲什麼《德雷爾一家》《萬物既偉大又渺小》提供了治癒的效果?他們和我們所追求的“進步”、追求的拜金文化格格不入——德雷爾一家因爲瀕臨破產才搬到了希臘科孚,住在破破爛爛的房子裏,空無一物,油漆剝落,天花板隨時可能掉下來。與碧海藍天相對應的,是原始閉塞和物質匱乏。而《萬物既偉大又渺小》裏,獸醫哈利早在上學的時候就被老教授警告過職業問題:如果決定將來做獸醫,生活中會有無窮的趣味和豐富的經驗,可是永遠不會成爲大富翁。這裏絕對沒有香奈兒不如愛馬仕的太太圈競賽,人們上街只是買點蘋果洋蔥,多煎一根香腸都算得上是美味餐點。
與現實中人們沉溺豐裕無法自拔的生活方式相比,劇集中的人物生活在上個世紀30年代,還沒有體會到人與物關係的徹底轉變,沒有極大的豐盛,也沒有戲劇性的浪費,普通的食品和物件都能夠成爲維繫人與人感情的牽絆。他們的生活也符合今天經歷過環境破壞之後人們的反思——那就是,不能漠視自然極限,保持尊重與剋制。
人際關係
沃斯特指出,在種種抵抗消費文化的力量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個體對地方羣體的認同。家庭也是一種對抗力量。德雷爾一家人密切關聯,相互關照,不僅以此應對惡劣的環境和貧困,也消除了彼此的孤獨感、不安全感和失落感。除了家庭,地方教會和一些團體也擁有這樣的力量,德雷爾一家努力參與地方教會、理解科孚島的風俗文化;對於獸醫哈利來說,賽馬場、舞會、酒吧也都是當地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沃斯特說,這種地方感,也可以讓人們在周圍的經濟文化轉向工廠、城市和過度消費時,思考當地社區的需要和生態和諧,從而“在隨風飄搖的文化裏穩如泰山”。

《德雷爾一家》第一季 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今天,個體已經被釋放到了都市的馬路和人行道上,人人都成爲了自己命運的主人。這些個體將如何共同生活?《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作者、社會學家基思·特斯特看到,懷舊/戀鄉提供瞭解決之道。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認爲,共同體是一種生命有機體,在規模較小、基本靜態的鄉村情境裏,共同體是顯著的。因此,當我們爲德雷爾一家的生活所着迷時,我們想念的不是田園牧歌時代受到界線限制的家園,而是其中所蘊含的確定性。在懷舊/戀鄉當中找到的解決之道,就是把個體維繫在某些限定的特性、身份、認同之上,現代性經過懷舊/戀鄉而變得可以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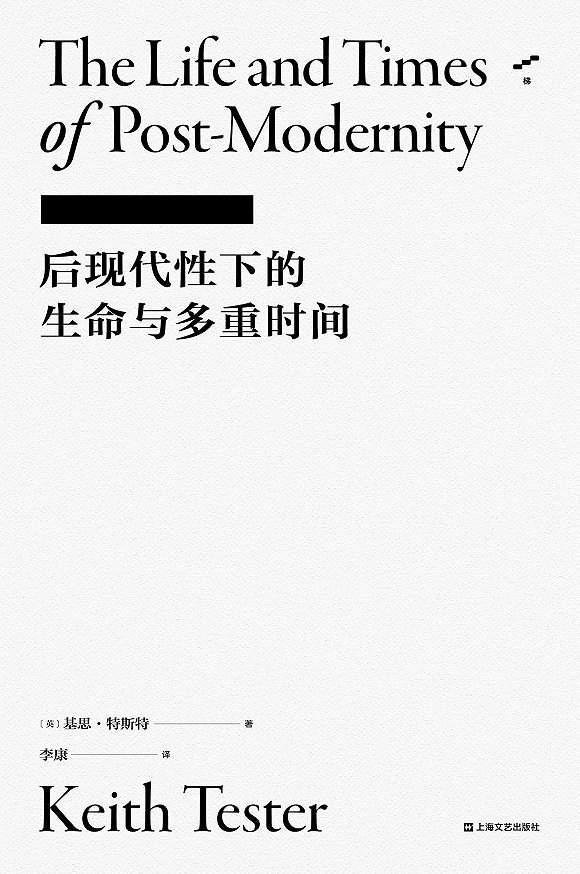
《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英]基思·特斯特著 李康譯 梯·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5
我們對田園生活的欣賞中蘊含着對現代性的批判。《森林紀》作者胡平看到,雖說英國作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代名詞,但是英國人心裏一直保持對鄉村的熱愛——哪怕他們一直居於城市,內心也始終嚮往着返歸鄉村。作者請求中國讀者自問:“如果說英國人的靈魂在鄉村,那麼,我們的靈魂去哪裏尋找呢?”
鄉村不是絕對的世外桃源之地,不然“打土豪,分田地”的階級鬥爭從哪裏來?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也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談到,對鄉村的田園牧歌般的想象遮蔽了問題,簡·奧斯汀筆下的村莊固然可愛,但主人公的鄰居們並不是住得最近的人,而只是社會地位上可以交往的人,在她的故事中,大量的農民是隱形的。舊日農村的“自然經濟”是一種剝削制度,人和土地一樣都是財產,多數人淪爲勞作動物,雖然農民也受到“保護”,但那只是爲了讓他們能夠付出更多勞動。即使是在“自然經濟”時期,鄉村也孕育着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地主階級逐漸演變爲資本家地主。隨後的圈地運動和農業資本主義使得鄉村和城市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即便如此,人們也對鄉村依然懷抱一種美好的想象,正如在村居者的眼裏城市充滿了誘惑。我們也必須生活在城市,才能夠想象鄉村的快樂。德雷爾一家、獸醫哈利給我們營造的治癒系的過去既不復存在,也無法再現,這其中的慰藉和失落卻讓人不由得意識到——我們正在對某些缺失的東西產生渴望。基思·特斯特說,或許,這種情結並不一定是拒斥當下,也可以是對於我們現在所處位置的一種積極的應對,讓我們針對物化的鬥爭變得更加堅定,重新獲得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和確定性。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