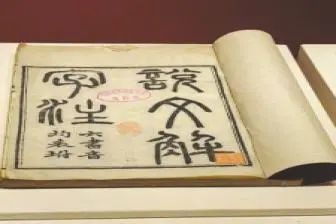索尼婭·薩哈近年來出版了多部與流行性疾病相關的書籍。2016年,她出版了《流行病:追蹤霍亂、埃博拉等傳染病》(Pandemic: Tracking Contagions, from Cholera to Ebola and Beyond);2010年,《發熱:瘧疾是如何統治人類50萬年的》(The Fever: How Malaria Has Ruled Humankind for 500,000 Years)問世。薩哈以小說的形式,爲讀者們講述了探索疾病傳播的故事,前者關於霍亂,後者有關瘧疾。
她在作品中對這些疾病追根溯源,偵探故事和報告文學的形式交融,引導着書中的“薩哈”和讀者們去到世界上某個遙遠的角落,回溯遠古的歷史。她的作品同樣也是帶有預見性的案例研究,歷史上有多少帝國趁疾病而興起,又因疾病而衰落,多少次繁榮的經濟因疾病而停滯不前乃至崩潰,薩哈就這樣通過她的作品,揭示出了人類在前進過程中與微生物的愛恨交織。
薩哈在新作《下一次大遷徙》( The Next Great Migration) 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人類遷徙背後的推動因素是什麼?這種大規模的遷徙是否更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穩定呢?事實上,這兩個問題與我們當今地緣政治的塑造緊密相關,所以薩哈的作品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內都依然具有預見性價值。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就有很多人預言,“大遷徙”的浪潮會重現,這也引發了許多人的擔憂。國家安全專家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Kaplan)在1994年《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其描述爲“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兩個超級大國加強了邊界的防控,人們也慢慢開始遷移。卡普蘭寫道,“聯合國大學的專家預測,到2020年,遷移的人口數將達到5000萬。環境安全分析師諾曼·邁爾斯預計到2050年,遷移的人口數將達到2億。而非政府組織基督教救援會猜測,到2050年,遷移的人口數甚至可能達到10億!”這些危言聳聽的預測導致了民粹政治的出現,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聲音:“禁止行動自由!”“修建邊境牆!”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們穩定下來。
在故事的一開始,薩哈對一系列自然觀察進行了描述,而這些現象都是來自自然界的預言。首先,薩哈觀察了格紋蛺蝶的行爲和習性。格紋蛺蝶主要棲息在美洲西岸,習慣低飛,且只有10天的生命。格紋蛺蝶並不是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物種,由於其對棲息地和環境的變化極其敏感,所以常常被當做是氣候變化的風向標。1996年,權威雜誌《自然》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稱隨着氣溫的升高,格紋蛺蝶的棲息範圍正在以每十年20千米的速度向北移動。薩哈也加入到了“追蹤者”的行列,見證並記錄了這一變化。同時,在追蹤格紋蛺蝶的過程中,她發現同樣的現象還發生在其他各種數不盡的物種當中,全球變暖迫使它們離開原有的棲息地,去尋找更適合生存的環境。例如,大西洋鱈魚也正在以每十年200千米的速度向溫度更低的兩級地帶移動。
薩哈承認,她的經歷與這種遷徙存在着某種相似關係。50年前,她的父母從印度移民到美國,以滿足紐約市對醫生的需求,這是來自印度次大陸的第一波合法移民浪潮。那次移民浪潮給薩哈帶來的是“一種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但是很不自在的強烈感受”。薩哈表示,“儘管我在美國出生,但我卻從不覺得自己真正屬於這裏;即便我已經在這裏成家生子,我依然覺得沒有真正融入其中。”薩哈和她的丈夫曾經搬到澳大利亞生活了幾年,他們成爲了雙重身份的“外國人”。這些感覺不禁讓薩哈思考:家的概念究竟從何而來?是後天學習而得還是我們先天既得的理解呢?
薩哈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終寫出了一部關於人類迫切地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的政治史。這一歷史起始於“線粒體夏娃”(mitochondrial Eve),她生活在大約20萬年前的非洲,被認爲是所有人類共同的祖先,隨後人類遷徙至世界各地,因此,她也被認爲是物種具有遷徙本性的起源。而歷史的尾聲結束於當代政治家們堅決而徒勞地否認這種本能,他們以難民爲例,認爲難民的遷移絕對不是出於本能,而是因爲無處容身,流離失所,只能去別的地方。

索尼婭·薩哈
構建完這段歷史之後,薩哈又對其進行了剖析。她認爲,當今人們對於移民的錯誤論述以及政治主流中再次出現的種族言論都是其造成的惡劣影響。20年前,比爾·克林頓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宣佈了人類基因組的排序。這項人類基因組草圖強有力地證明了人類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多過那些讓我們分裂的不同點。通過測序儀,我們發現,串聯在我們DNA鏈條上的30億個核苷酸中,僅有0.1%的不同,而深深烙印在我們基因當中的共同點,正是自古以來便存在於人類本能之中的對於交融和遷移的渴望。
在研究接近尾聲之際,薩哈談到了她的歐洲之行以及對難民問題的一些見聞和看法,揭露了政客們是如何不遺餘力地否認這種遷徙的本能的。在希臘萊斯博斯島上,掘墓人將一波又一波的難民(大多數都是孩子)埋葬在無名的墳墓中,他們被海水衝上海岸,無從得知身份,但洶涌的愛琴海依然擋不住奔赴歐洲的難民潮。這一切很難解釋,只能說我們所瞭解的生物學,和歷史與政治家們所宣揚的那一套截然不同。薩哈堅持認爲: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