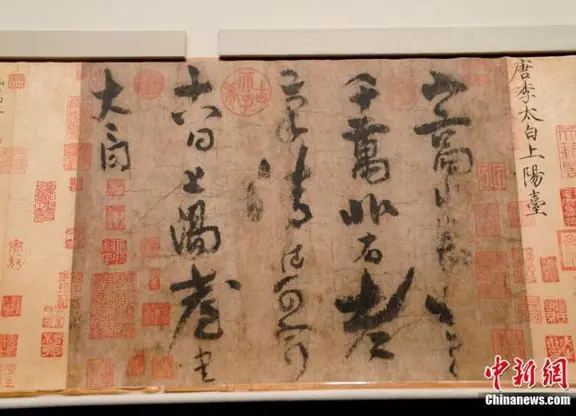希拉里·曼特爾
英國作家,兩屆布克獎得主,代表作爲“都鐸三部曲”

希拉里·曼特爾的新作《鏡與光》
如果現在你想讓自己振作起來,而不是舒緩心情安慰自己,你可以開始讀或重讀艾維·康普頓-伯內特的小說——如果你喜歡她,有19本小說供你挑選。在我二十幾歲時,我第一次閱讀了她的作品,但因爲感到困惑並且有點兒反感她的風格,我半途而廢了。但當十年後我再次閱讀她的作品時,我卻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私心希望那是因爲我開始自己寫作,並開始欣賞她那行文中冷酷無情的對白,而不是因爲我像她文中的角色那般冷酷無情。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反覆拜讀她的文章。
我並不太在意選了哪本書讀。它們都大同小異: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家庭,通常都是幾代共居,吃飯時會相聚在充滿腐敗氣息的鄉間小屋。在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餐時,他們彼此挖苦。書中會有幾個殘暴的掌權者和天生的受害者,還會有和事佬、天真的人、循規蹈矩的人,以及一些攪局的流言蜚語,由僕人們組成的合唱團,他們那易怒和滑稽的世界是那些坐在樓上看戲的上流社會的倒映。
簡而言之,這就是讀書人的《唐頓莊園》。故事情節很荒謬:字裏行間都是投毒殺人、血親相姦。我不需要看着作者把她的天賦浪費在謀篇佈局上,也許就是我喜歡這些作品的一個原因。你可以大致猜到會發生什麼,但當你一句一句讀下來,你會盯着那一頁眨眼:“她真的這麼說了嗎?”
要找到康普頓-伯內特的書並不是那麼容易——新版的書很少,甚至有一些是有聲讀物而非實體書,否則你就必須買二手的,還得在書頁掉出來的時候保持耐心。在她有生之年和身後的日子裏,作品的出版情況都很糟糕,因此那些關注細節的人可以在閱讀過程中,做一些裝訂和校對工作。我最大的願望是組建一個粉絲俱樂部,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更美好的日子裏一起用餐,用冷笑的警句和含蓄的侮辱來互相鼓勵。比如《男僕女婢》( Manservant and Maidservant )《大宅和總管》( A House and Its Head )都會是很好的切入點。
另一個不爲大家所知的是安東尼·鮑威爾的作品。他的12卷《與時代合拍的舞蹈》( 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 )剛由企鵝出版社重新發行。但有時我需要從紙墨味中逃離,香水是一種可以提升心情的藝術。所以我搜集着我所有的香水小樣和瓶中的剩餘香水,這樣我就每天都用不同的香水。香水對生命的意義,遠不止防腐。
馬克·哈登
英國作家,代表作爲《深夜小狗神祕事件》

馬克·哈登
由於長期的情緒紊亂和拉莫三嗪(治療癲癇的藥物)不時的失效,我的生活反覆經歷黑暗時期。我很想炫耀說,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就會開始重讀斯科特·蒙克里夫翻譯的普魯斯特作品,或是第27次看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但說實話,我在那種狀態下什麼都讀不進去,我焦躁到無法看完整部電影。我需要的是大聲播放的音樂,特定的音樂。有一年多的時間,從我醒來到一直到我睡去,我都害怕自己會死去,在這期間我只能聽藍靛女孩樂隊(Indigo Girls)或莫扎特——除了D小調安魂曲,考慮到這是一首爲死者而作的彌撒曲,而莫扎特害怕這會成爲他爲自己葬禮所作的譜寫,因此他沒有寫完這首曲子,因爲害怕自己會在創作中途死去。
去年我做了三次心臟搭橋手術。在整個過程中,我竟然挺開心的。但在手術後的幾個長夜裏,我確實需要音樂的陪伴,尤其是在我肺衰竭和止疼藥效果消退的時候。在這期間,有兩張專輯成了我的至交——第一張是Autechre的《NTS Sessions》,一張完全不商業的專輯,且部分曲目是由電腦寫的。
我可以幾乎百分百肯定你不會喜歡這張專輯,但對我來說,它卻扣人心絃、十分誘人並不斷昇華。它完全是在電腦上創作的,沒有聲學樂器,沒有錄音室,沒有音樂廳,不屬於任何藝術流派。它似乎佔據了物質世界之外的一個地方:我想我會漂浮起來,想象巨大的飛船在太空深處緩慢移動。鑑於當時我也佔據了物質世界之外的一個地方,音樂似乎以某種模糊的方式與我相關。
第二張專輯是主要由中提琴演奏家、編曲家約翰·梅特卡夫創作的旋律音樂唱片《色彩的出現》(The Appearance of Colour)。這張專輯和麥克斯·裏希特的作品很像,但比之更有趣的是,它給你類似於在深夜開車的時候,會在第三電臺(Radio 3)的廣播節目《午夜路口》中聽到的東西,它讓你心中生出“啊!我的生活中需要這樣的東西”的想法。此後我在需要安慰時,我就常常會聽這兩張專輯。一方面是因爲它們內在的奇妙,另一方面是因爲在醫院的經歷使我對它們產生了像嗎啡一般的依賴,我不得不說,這種“嗎啡依賴”並不令人不快。
奧利維亞·萊恩
英國作家,2011年麥克道爾獎得主,代表作有《回聲泉之旅》《沿河行》《孤獨的城市》等

奧利維亞·萊恩
上週我心情低落時,我的朋友菲利普給我發了一張大衛·鮑伊的照片,這是一張從背後拍攝的照片,他穿着一件黑色緊身毛衣,橘黃色的頭髮向後梳着,正在牆上畫着一個圓圈。在圓圈上面,是一個用紅色塊狀字母寫的單詞ISOLAR(隔離)。他就在那裏,我的隔離期守護神。從我青春期的時候,鮑伊就佔領了我的臥室,我會在房間裏跟着他的歌聲一起大唱《The Bewlay Brothers》。當時,他似乎遠遠領先於我們其他人,他的歌聽起來就像是來自外太空一般。現在,在2020這個瘟疫之年,我很欣慰地發現《天外來客》(鮑伊主演的電影)中的外星人現身於此,在昏暗的吊燈下,在一個鋪着森林牆紙的地下室裏打乒乓球,度過了他與世隔絕的日子。
他的許多歌曲都描述着遠超人們想象的困境,以及無法找到的回家的路。我現在想聽的就是那段一個外星人呼喚自己同類的樂句。但是當我聽的時候,作爲人類的回憶如潮水般涌入進來。和我妹妹一起看《迷宮》時,我被鮑伊扮演的孤獨性感的哥布林國王迷住了。在一個春天的深夜,我和朋友約瑟夫一邊聽着《Heroes》,一邊開車穿過布朗克斯。我們充滿欣喜的開上了通往曼哈頓的大橋,彷彿我們擁有了整個世界。
我現在不這麼想了,但我剛剛在YouTube上看了一段鮑伊和瑪麗安·費弗爾合唱的《I Got You Babe》的視頻。瑪麗安·費弗爾打扮成修女,鮑伊則穿着漁網襪、羽毛和紅色乳膠服。他看起來像蛇一樣充滿野性,骨瘦如柴,他無法停止發笑,也許是因爲他心情愉快,也許是因爲他喜歡他那可笑而又華麗的表演。看到他這樣蹦蹦跳跳讓我覺得很舒服,一個輕巧愉悅的藝人,顛覆了地心引力,讓你飄飄欲仙。
艾麗夫·沙法克
土耳其小說家,代表作包括《神祕主義者》《愛的四十條法則》《名譽》《伊斯坦布爾孤兒》等

艾麗夫·沙法克
我甚至不再思考。這種恐慌狀態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情緒,也影響着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的壓力越來越大,心情沮喪、無精打采。
或者我們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強迫自己變得因沒心沒肺而開朗,這也是有問題的。當一種病毒在如此多的國家裏無情地屠戮着世界上最脆弱的人,而我們的統治者又是最糟糕的民粹主義者時,我們不能簡單地關上通往外界的大門,退到藥草園中安心種植迷迭香和牛至。我們不能麻木於別人的痛苦。
但是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迷迭香和牛至的確很重要,雖然它們是我們生命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但是它們卻能賦予我們歡愉,並讓我放鬆心情。其實我要問的問題是:如何尋找恰當的平衡?我們如何與人類同胞保持聯繫,承認悲傷的現實,持續關注新聞,爲社會做出貢獻並幫助他人,同時保持並感謝生活中那些所謂“平凡”的快樂(花香,一天中第一杯咖啡的味道)?我們如何才能把光明和黑暗同時放在心裏呢?
我打小就對哥特文學、音樂和文化很感興趣。在哥特王國中,各種辯證對立的事物不斷地相互交織和交流——快樂與憂鬱、想象與現實、希望與沮喪、美麗與衰敗。對我來說,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爾維諾——還有雪萊、坡、洛夫克拉夫特——都是我的心頭肉。同樣,阿倫特、本雅明、阿多諾,然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安娜·阿赫瑪託娃,他們彼此的寫作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他們有所不同但又辯證統一。
我還經常一遍又一遍地聽哥特金屬音樂、工業金屬音樂、異教金屬音樂、前衛金屬音樂和金屬芯音樂,還會把音量調得很高。在這些流派中,相反的情緒彼此交融如天作之合。每當聽到這些音樂,我想我追求的並不是徹頭徹尾的悲傷或徹頭徹尾的歡愉,而是在尋找能夠將兩種情感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作品,這就是爲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哥特作品的懷抱。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