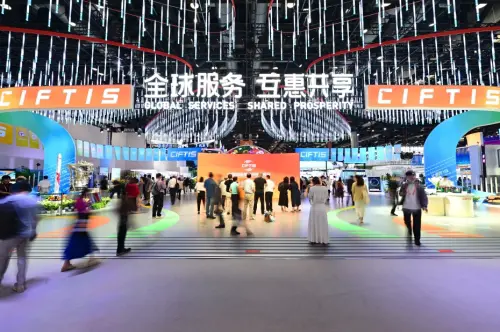看《愛爾蘭人》的時候,一直有個疑問縈繞心頭。爲什麼時間過去,弗蘭克·希蘭(羅伯特·德尼羅飾)的女兒們都長大了,三個出場就是老年人的男主角還是那個樣子。
減齡技術對德尼羅、阿爾·帕西諾、喬·佩西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留給觀衆這樣的錯覺:他們活在自己的時空裏,時代變遷和紛繁歷史事件動不了他們一根汗毛。
或許馬丁·斯科塞斯是故意的,沒用起用年輕/年長兩批演員跨越角色的不同年齡段,減齡技術也未過火。在三個半小時的長度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大事件如流水,這三個老頭就像水中磐石,以老年人特有的遲鈍置身其中。他們與時代的關係很值得反覆品嚐。
《愛爾蘭人》講了個簡單的故事:卡車司機弗蘭克被黑幫大佬羅素(喬·佩西飾)賞識。他爲黑幫效力,“刷牆”(殺人)和“做木工”(處理屍體)。後來羅素安排他保護工會主席吉米·霍法(阿爾·帕西諾飾),二人亦建立友誼。霍法與羅素鬧翻後,弗蘭克受命祕密幹掉霍法,造成美國史上最大懸案之一——吉米·霍法失蹤案,至其死前方吐露真相。
圍繞着他們出沒着衆多角色。有的匆匆而過,有的反覆出現直到最後。他們蠅營狗苟,行事受本能驅使,一副面孔配一副心腸,沒有心計深厚之徒。他們碌碌一場,慾望吞了良心。這些角色聚在一起,玩了一場屬於他們自己的遊戲。他們深度參與歷史進程,又好像一羣幽靈,其實什麼都沒改變,就一個接一個消失了。
愛爾蘭黑幫與美國政治、工會的深度勾連由來已久。美國曆史上,三分之一的總統爲愛爾蘭裔或有愛爾蘭血統,影片中的肯尼迪家族便是愛爾蘭裔勞工起家。總統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爲第三代愛爾蘭移民,家族在禁酒令期間通過販賣私酒致富,與黑幫關係密切。靠私酒生意壯大的另一個團體是卡車司機。壟斷私酒業的黑幫需要卡車運輸,卡車司機工會需要黑幫的力量與企業主對抗。互相需要的雙方結成同盟關係,影片中的黑幫殺手弗蘭克後被霍法委以重任,擔任工會負責人是當時的常態。據統計,1957年全美最重要的57個黑幫頭目中有22個是工會負責人。
這部電影的一個特點是,它根據查爾斯·勃蘭特的《愛爾蘭人》爲原著藍本,形成奇特的歷史觀。這本書是勃蘭特對弗蘭克·希蘭的數百小時訪談寫成,它出自一個人的視角,有時與官方認定的歷史有出入。
知悉官方歷史的觀衆未必全盤接受弗蘭克的說法。比如,弗蘭克認爲肯尼迪派兵入豬灣欲推翻卡斯特羅是爲了方便黑幫重新掌握古巴賭場;暗示吉米·霍法很可能派人刺殺肯尼迪總統,以拔除掉肯尼迪兄弟這對眼中釘。
你相信歷史的哪張面孔?私人視角與正統視角重疊,真真假假,歷史成了萬花筒般的有趣之物。卸下沉重,斯科塞斯用流暢的長鏡頭和輕快節奏帶我們遊走於這條變幻多端的長長甬道。
故事就這麼快速地一頁頁翻過。《愛爾蘭人》,也就是弗蘭克提供的視角既務實又荒誕。其中有傻子不經意間把歷史撞向另一個方向(霍法的養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他的謀殺),亦有聰明人一世經營終於喪失(霍法還是沒能坐回卡車工會主席的位子)。
世間的重大事情多是這樣發生的,不是來自精心算計,而是出自草率與巧合。
出場便衰老的三位男主角既是旁觀者和親歷者,也是幫助我們進入另一個世界的線頭。

跟隨他們,我們進入一個純真的世界。我以爲黑幫片最迷人處正在於此。
弗蘭克·希蘭、羅素·巴弗利諾和吉米·霍法,這三個老硬漢的使命和命運軌跡各能以一語概之:弗蘭克一直在殺人,羅素一直在擺平黑幫事務和收錢,霍法一直在竭力保住工會主席的位子。
他們之間滋生友誼的方式與兒童相似:羅素幫弗蘭克修車,他們一起吃麪包蘸紅酒,講意大利語(羅素是意大利黑手黨);弗蘭克作爲保鏢與吉米住一間套房時,他睡客廳沙發,吉米的房間總是留一條門縫。
杜琪峯拍了那麼多黑幫片,《槍火》裏幾個西裝革履的男人執行任務時百無聊賴在辦公室踢紙團的一幕,始終最動人。嚴酷的環境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讓友誼和童心萌芽,雖然這朵小花註定要被摧毀。
後來羅素與霍法的交惡過程也非常幼稚。他們通過弗蘭克這個中間人屢次傳話,威脅、反威脅,跟小孩子鬥嘴皮子時的一根筋一模一樣。只不過,孩子鬥完嘴很快就和好,而羅素決定幹掉霍法。
他們翻臉的原因很簡單,成年人趨之若鶩的錢、權和名譽讓兩個老小孩從兒童友誼驟轉爲成人間的你死我活。
在這之前,《愛爾蘭人》的基調輕鬆幽默。每個人的行動都彷彿直接從身體最深處直接反映到動作上,往往重複而機械。這種心靈的缺席是黑色電影中的常見氛圍。固定機位拍弗蘭克一次次執行完任務往河裏扔槍,成爲這種機械性的極致。戴眼鏡的殺手、吊兒郎當脾氣暴躁的黑幫頭目安東尼、喜歡吃牛排的黑幫小頭目Skinny等角色皆是如此—重複,執拗,幼稚可笑。
在這樣的對比下,獄中羅素對弗蘭克吐露的一絲後悔(“吉米是個好人”);弗蘭克得知羅素的殺意後久久盯着他看,他半夜欲打電話通知霍法卻未行動;霍法隨弗蘭克赴約,看到空房間心知不妙讓弗蘭克快走時,這鍋文火慢煲的湯立即有了四兩撥千斤的力量。

加上馬丁·斯科塞斯,《愛爾蘭人》的四位重要角色都是老人。老人自然會想到死亡。
斯科塞斯用死無大小好歹,人人平等的方式表現死亡。電影中不管多小的人物,只要死於非命,斯科塞斯都會通過直接表現或爲其打上死亡詳情的字幕來告知。
到了最後,和弗蘭克一起玩遊戲的人都死光了。他爲自己選棺材,要綠色的,因爲他是愛爾蘭人。不要火葬和土葬,要逼仄地葬入一堵牆,因爲其他的葬儀都預示着終結,而他覺得故事未完。
那些角色的突然死亡,一種說法是與肯尼迪總統遇刺有關。官方“系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爲”的說法不確切,與案件有染的人證或遭到滅口,共115人。
這條充滿懸念的線索貫穿整部影片,像死亡的手錶滴答滴答。對弗蘭克來說,這些一個接一個滅掉的燈把他推入逐漸孤絕的處境。當他得知自己的律師也死了,脫口而出“是誰殺了他?”時,弗蘭克的處境已經成爲老人們的普遍狀況。
他這一代人的後代們與他們關係疏遠,更談不上延續。吉米·霍法的傻兒子始終矇在鼓裏,不知父親死亡的真相。弗蘭克·希蘭聰慧的女兒早就察覺是他殺了親愛的霍法叔叔,從此再也沒和父親說過一句話。
這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結局。幽靈般穿過歷史,結束一生。
(來源:澎湃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