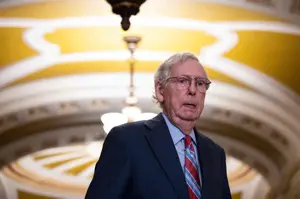卜鍵新作《庫頁島往事》的創作絕對是受到俄羅斯大文豪契訶夫《薩哈林旅行記》的“刺激”與影響。這不是我的主觀臆測而是卜鍵的夫子自道,他在該書開篇的“引子”中就直言,這次創作是“跟隨契訶夫去觸摸那片土地”,“曾經的我對庫頁島幾乎一無所知,正是讀了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才引發對那塊土地的牽念”。“庫頁島的丟失,原因是複雜的……而我更多反思的則是清廷的漠視,包括大多數國人的集體忽略。這也是閱讀契訶夫帶來的強烈感受,僅就書生情懷而言,爲什麼他能跨越兩萬裏艱難程途帶病前往,而相隔僅數千裏的清朝文人從未見去島上走走?”
那麼,對卜鍵形成如此強烈刺激的《薩哈林旅行記》究竟又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呢?本人大學讀書時曾經閱讀過,但現在回想起來,它究竟寫了什麼已模糊不清,而且這部作品在契訶夫畢生的創作中有着什麼特殊的價值當時也是渾然不覺,倒是對他的《第六病室》和《萬尼亞舅舅》這樣的小說、戲劇代表作更重視。爲了更好地理解卜鍵的這部《庫頁島往事》,我又買了一本最新版的《薩哈林旅行記》重讀。對該書的評價當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關於它究竟歸屬於哪種門類倒是引發了我的一點好奇。在今年元月剛推出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薩哈林旅行記》的版權頁上,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中心給它的分類是“遊記”。這當然也未嘗不可,它畢竟是契訶夫一八九○年四月自莫斯科出發歷時近三個月、行程萬餘公里,在薩哈林島上連續生活遊歷了八十二天後纔有了以這段經歷爲題材的《薩哈林旅行記》,而整部作品的創作又是耗費了三年時光才最後定稿。
從整個創作過程及作品題材的外觀看,稱其爲“遊記”雖不爲過,但再往深裏細想,作爲契訶夫畢生唯一的非虛構,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險、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的這次創作,難道僅僅是爲了寫一部“遊記”嗎?這似乎有點古怪。據研究者考據,契訶夫在這次遠行前一年的冬天就有了創作這部作品的念頭,他想知道那片苦役之地的模樣,想了解俄羅斯刑罰體制的真實面貌。於是他像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調查專家,設計了一種簡潔易用的人口調查卡片,用來採訪全部苦役犯、流放犯和定居者,因而在後來的創作中才有了對數據的大量應用。也正因如此,無論是創作中的契訶夫還是出版時的編輯與出版商,一時皆不知究竟該給此書如何定位,這其實很正常,也就有了後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定位:有的將其視爲某種人類學或民族誌,有的將其稱爲專題調查新聞,有的將其當作科學報告。客觀地說,這些概括都各有其理各有其據。
契訶夫此次遠東之行還有一個特點便是當局不允許他接觸島上的政治犯,回過頭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遺憾,但客觀上又導致了《薩哈林旅行記》呈現出一種非政治化的特徵。由於他接觸的都是些刑事犯,而刑事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但在契訶夫眼中,刑事犯也是人,因而,這部作品一個突出的特徵便是充滿了強烈的人文關懷,這就使得整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社會或田野調查而具有了強烈的人文色彩,“人”而非“島”纔是這部作品的主角。也正是由於這一點,《薩哈林旅行記》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潛在的跨界寫作”。這個描述當然是我的一種杜撰,即外觀上雖爲“遊記”,但骨子裏則是一次特別而艱辛的人文創作之旅,這種“潛在的跨界”使得《薩哈林旅行記》成爲契訶夫畢生創作中一部“特別特”的作品。
似乎扯遠了,還是回到本文討論的主體——卜鍵的《庫頁島往事》上來。還真是無獨有偶,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中心給它的分類是“薩哈林島-介紹”,這有點像是將其歸爲地理知識一類。從作品表層看,這也沒錯。在作品第二章的開篇卜鍵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庫頁島南北延綿近兩千裏,東西最寬處逾三百里,面積大約七萬六千平方公里,超過臺灣地區與海南島的總和,曾爲我國第一大島。島上有高山大川,密林廣甸,大量的湖泊沼澤,豐富的煤炭和石油礦藏,尤其是久有漁獵之利。又以東北臨鄂霍次克海,南與日本的北海道隔海相鄰,有着重要的戰略地位。”這樣的文字確是貨真價實的地理知識介紹,但我以爲,如果從整體內容看,將其歸入“中國歷史研究”一類比“地理”類或相對更妥帖。
作爲專治清史的學者,卜鍵從事歷史研究很正常。在邊疆研究史專家馬大正看來,《庫頁島往事》“是填補研究空白的著作”,“是一部嚴謹的學術探研著作”,“以後只要研究庫頁島,這本書就不可小覷”。同時,他還做了一個初步統計:“從附錄參考文獻類的書目來看,涉及文獻檔案的彙編就有四十九種,一種可能對應一本,也可能對應幾十本、上百本。卜鍵把有關史料記述基本上一網打盡,這很不容易。”的確,在《庫頁島往事》中,有關庫頁島歷史的研究,卜鍵的貢獻至少涉及三個十分關鍵的方面:一是通過對各種散見史料的細緻爬梳,釐清了庫頁島居民的構成及其與中原的關係;二是考據了庫頁島究竟從何時起脫離了中國的懷抱,卜鍵認爲“從法理上說,可追溯到整整一百六十年前的《中俄北京條約》”,“然細檢《中俄北京條約》文本,其中並沒有出現庫頁島的名字,再看兩年前奕山所籤《璦琿條約》,也完全不提這個近海大島”;三是由此進一步追尋庫頁島丟失的複雜原因,更多地反思“清廷的漠視”和國人的忽略。
但是,上述這種嚴謹的歷史考據與研究畢竟又只是《庫頁島往事》的“半壁江山”,頂多也就是“多半壁”,而且它明顯不同於我所讀到過的衆多歷史研究專著,那些作者的所爲一般都只是在那裏冷靜地發掘考據陳列史料史實,追求的是言必有據,至於作者自己的立場則往往隱身於這種史料的挖掘與選擇背後。而卜鍵在《庫頁島往事》中則有太多的作爲歷史研究中所不常見的個人主觀情感代入,這個作者一不小心就要自己蹦出來或痛心疾首,或撕心裂肺地抒發一下自己的情感,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急切溢於言表,個體情感的代入絲毫不加掩飾。正因如此,也就無怪乎有學者稱其爲是一種“歷史散文”的寫作。而且,《庫頁島往事》在敘述上也的確呈現出一種明顯的雙線結構,即一條是種種散見史料的鉤沉爬梳,另一條則是契訶夫《薩哈林旅行記》中的庫頁島。前者是史料中的所謂“客觀”,後者則是一位大作家筆下貌似“客觀”的主觀,兩相碰撞,就使得《庫頁島往事》如同《薩哈林旅行記》那般也呈現出一種“潛在的跨界寫作”狀態,所不一樣的只是“跨”的起點與落點不盡相同,前者從“遊記”跨入“人性”,後者則是“史實”與“文學”的雙跨,都跨出了一番別樣的風景。
所謂“潛在的跨界寫作”,只不過是個人閱讀直觀感覺的一種描述,我無能就此做出若干學理性的闡釋。但我想無論是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還是卜鍵的《庫頁島往事》,從某種門類寫作的客觀要求與事實上的主觀呈現之間存在的差異是明顯的,而導致這種明顯差異的一個重要緣由就在於他們那種潛在的“跨”,也就是超越了一些既定的常規。這種超越既沒有造成知識的硬傷,讀者閱讀起來也不感到突兀,相反倒是作者的這種主觀情感與意志的介入更容易讓讀者感受到一種新奇、產生了一些震動、引發出若干思考……如此這般,也就有理由爲之點個贊喝個彩吧!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