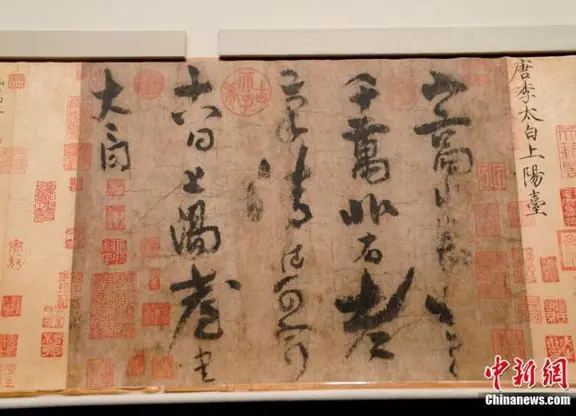人們往往會對祕密的披露感到欣喜。或者至少可以說,媒體機構已經意識到,諸如“謎團被解開”和“隱藏的寶藏被揭示”之類的新聞會帶來流量和點擊率。因此,當我(指本文作者Sonja Drimmer)看到人工智能輔助得出的、關於著名大師的藝術作品的新發現成爲熱點話題時,我從不感到驚訝。
僅在過去的一年裏,我看到一些文章稱人工智能恢復了意大利畫家莫迪裏阿尼(Modigliani)的“失落的情人”的“祕密”畫作,讓“隱藏的畢加索的裸體繪畫重煥生機”,“復活”了奧地利畫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被毀的作品,“恢復”了倫勃朗1642年畫作《守夜》的一部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作爲一個藝術史學家,我對這些項目的報道和傳播越發關注。實際上,它們並沒有揭示祕密或解決謎團,它們所做的是創造讓人們對人工智能產生良好印象的故事。
我們真的學到了任何新東西嗎?
以有關莫迪裏阿尼和畢加索畫作的報道爲例。這些項目是由同一家公司Oxia Palus執行的,該公司不是由藝術史學家而是由機器學習領域的博士生們創立的。
在這兩個案例中,Oxia Palus採用了傳統的X射線、X射線熒光和紅外成像技術,這些技術在幾年前就已經被髮表並投入使用了——這些工作揭示了藝術家在畫布可見層下的初步繪畫。
該公司對這些X射線進行了編輯,並通過應用一種稱爲“神經風格轉移”(neural style transfer)的技術,將它們重新組合爲新的藝術作品。這是一個聽起來很複雜的術語,指的是將藝術作品分解成極小的單元,從中推斷出一種風格,然後以同樣的風格重新創建其他內容的圖像的技術。
從本質上講,Oxia Palus將機器從現有的X射線圖像和同一藝術家的其他畫作中學習到的東西拼製成新作品。
但是,除了發揮人工智能的威力之外,該公司所做的事情,在藝術上、歷史上是否有任何價值?這些重現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我們不知道的關於藝術家的信息和他們的方法。
藝術家總是在他們的作品上一層疊一層地作畫,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藝術史學家和文物管理員創造了一個專門的詞來描述這種情況——Pentimento。這些早期的創作並不是像復活節彩蛋那樣存放在畫中供後來的研究人員發現的。最開始的X射線圖像當然很有價值,因爲它們提供了對藝術家工作方法的洞察力。
但在我看來,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這些項目所做的事情並不完全具有新聞價值。
急需支持的人文科學
因此,當我看到這些複製品吸引了媒體的關注時,我覺得這是爲人工智能所做的軟性營銷,在對人工智能的欺騙、偏見和濫用的懷疑情緒上升的時候,這些新聞展示了對該技術的“文明”應用。
當人工智能因重現丟失的藝術品而受到關注時,它讓自己聽起來沒有之前那麼可怕了——曾幾何時,它創造了僞造政治家言論的深度假象,還因利用面部識別進行專制監視而上了新聞頭條。
這些研究和項目似乎也強化了計算機科學家比藝術史學家更善於進行歷史研究這一認知。多年來,大學人文科學部門的資金逐漸被擠壓,更多的資金被輸送到科學領域。由於科學聲稱其具有客觀性和和能得出經驗上可證明的結果,它們往往從資助機構和公衆那裏獲得更大的尊重,這爲人文學科的學者採用算法提供了激勵。
藝術史學家克萊爾·畢曉普(Claire Bishop)批評了這一發展,指出當計算機科學融入人文學科時,“理論問題被數據的重量壓扁了,”從而產生了非常簡單化的結果。從根本上而言,藝術史學家研究藝術曾經如何向人們提供看待世界的洞察力,探索藝術作品如何塑造了它們所處的世界,並繼續影響後代。計算機算法不具有這些功能。
然而,一些學者和機構已經允許自己被科學所淹沒,採用他們的方法並與他們在受到贊助項目中合作。文學評論家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警告說,不要向科學讓步太多。在她看來,科學和人文學科並不是它們經常被描述成的那種二元對立的關係,但這種描述對科學是有利的——科學因其所謂的清晰性和實用性而受到推崇,而人文科學則被認爲晦澀和無用。她還稱,融合藝術和科學的混合研究領域可能會帶來突破,但這些突破不可能作爲一個孤立的學科存在。
我對此持懷疑態度。這並不是因爲我懷疑擴大、多樣化我們的工具箱是一件有用之事。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從事數字人文科學的學者已經以微妙的方式和歷史意識接受了算法,從而微妙地改寫了某些根深蒂固的敘事,或乾脆推翻了這些敘事。
我揮之不去的懷疑來自於這樣一種意識:公衆對科學的支持和對人文學科的輕視意味着,在努力獲得資金和接受的過程中,人文學科將失去使其至關重要的東西。該領域對歷史特殊性和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得將同樣的代碼應用於廣泛不同的人工製品這件事顯得完全不合邏輯。
認爲100年前的黑白照片會和現在的數字照片具有相同顏色這件事是多麼的荒謬。然而,這正是人工智能輔助着色的作用。這個特殊的例子可能聽起來像是一個疑慮。但這種“讓作品重煥新生”的努力經常會把表象誤當作現實。添加顏色並不顯示事物的本來面目,而是以我們自己的想象重新創造已經存在的東西——一張照片,現在有了計算機科學的批准印章。
藝術是科學家沙盤上的玩具
最近有一篇論文專門討論使用人工智能分解揚和休伯特·凡·艾克的《根特祭壇畫》的X射線圖像,在該文的結論附近,撰寫該論文的數學家和工程師提到他們的方法依賴於“選擇‘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這是伏爾泰的原話),採取兩個獨立運行的第一個輸出,只在輸入的順序上有所不同”。
也許,如果他們對人文科學有更多的瞭解,他們就會知道,當伏爾泰用這些話來嘲笑一個認爲猖獗的痛苦和不公正都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的哲學家時,這些話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世界的現狀代表了我們所希望的最好結果。也許這個用典有些廉價,但它說明了藝術和歷史成爲沒有受過人文學科訓練的科學家的沙盒玩具的問題。
別的姑且不說,我希望報道AI的這些發展的記者和評論家能對它們投以更多的懷疑眼光,並改變當下的AI的發展方式。在我看來,那些負責向公衆傳達這些研究結果的人,與其把這些研究當作英雄般的成就,不如把它們看作是質疑計算科學在擠佔藝術研究時正在做什麼的機會。他們應該問,除了人工智能、其最狂熱的支持者和那些從中獲利的人之外,這一切是否有利於任何人或任何東西。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