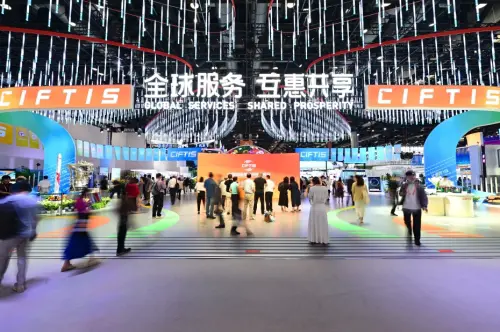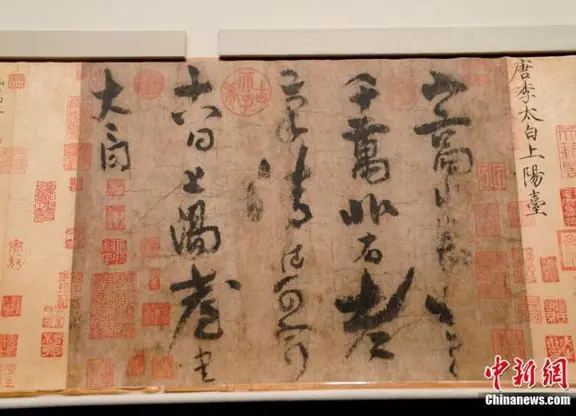大約每一千個產後媽媽中,就會有一個遭受產後抑鬱症的折磨。然而,“產後抑鬱”的問題至今依然不受大衆的重視。或許,正如勞拉·多克里爾(Laura Dockrill)在她的回憶錄《我都幹了些什麼?》( What Have I Done? )中所描寫的,產後抑鬱患者往往會因爲自身的抑鬱而感到辜負了自己和孩子,她們被深深的愧疚和自責籠罩着,最終只能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而她們的遭遇也很少爲大衆所知。直到這兩位優秀的女性作者通過作品坦陳了自己噩夢般的親身經歷,人們才得以一窺“產後抑鬱”的真相。
凱瑟琳·喬(Catherine Cho)的自傳《地獄》( Inferno )描寫了她在精神病房接受治療的兩個星期裏的經歷,能讓讀者感受到強烈的衝擊力,並喚醒你以陌生人的視角重新認識自己。凱瑟琳的文筆簡潔而隱晦,並將韓國的民間傳統和家族歷史穿插在故事中。“疏離感”是貫穿全文的主題——過去,她的祖父母因抗美援朝戰爭而與家人朋友們永久分離;後來,凱瑟琳和她的丈夫詹姆斯成了美國移民,而當凱瑟琳的孩子出生時,他們已移居倫敦。
凱瑟琳寫道,“很難說我的抑鬱症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是我兒子出生的那一刻嗎?還是說早在幾代人之前,它就已經深深根植在我們家族的命運中呢?”這些關於命運的問題在全書中反覆出現,這是產後抑鬱患者身上一種特定的共性,她們被偏執的念頭和責任感困擾着:“這是我造成的嗎?是不是我的錯?”因爲違背了所謂的韓國傳統的生養習慣,凱瑟琳的遭遇被家族視作罪有應得。但是,凱瑟琳說,“我不明白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在意那些傳統,在我看來,那些都是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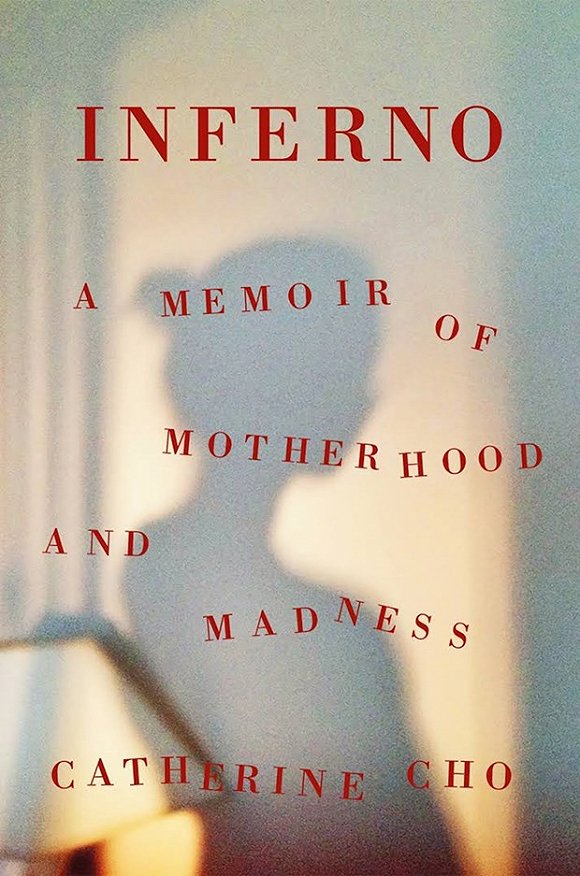
《地獄》
然而她漸漸失去了對現實的掌控能力,抑鬱的折磨也讓她越來越相信自己被困在了煉獄之中。她開始將關注點轉向自己和丈夫的家族病史,企圖從這個方面尋求答案。鬼神、命理、轉世和神話都是她文化傳承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今已然滲透到了她的日常生活當中,精神病院裏的醫生和護士在她看來就像是魔鬼和天使。
在醫院接受治療時,凱瑟琳不停地穿梭在現在和過去的時光中。她一面持續記錄當下的片段,試圖拼湊起記憶的碎片,找回真正的自己;一面從遭受虐待的童年一路回憶到結婚生子,試圖找出造成自己抑鬱的源頭。凱瑟琳在書中對於自己一步步走向抑鬱的過程的描述,讀來讓人倍感驚悚和瘋狂。凱瑟琳平靜而穩重的敘述口吻就更讓人感到恐懼了,幾乎難以相信這本書竟然是她的處女作。
在《我都幹了些什麼?》一書中,詩人兼兒童文學作家勞拉·多克里爾也深刻描繪了產後抑鬱給她帶來的偏執和錯亂,並通過自身的經歷,讓讀者確信那種抑鬱的感覺只有自己能夠深切體會,別人甚至無法相信。多克里爾詳盡描寫了分娩時女性所經歷的混亂和脆弱,簡直令人窒息。她毫不畏懼地描述了那種好似淪爲動物的感受,面對失禁的難堪以及分娩過程中難以言喻的疼痛,她無能爲力,只能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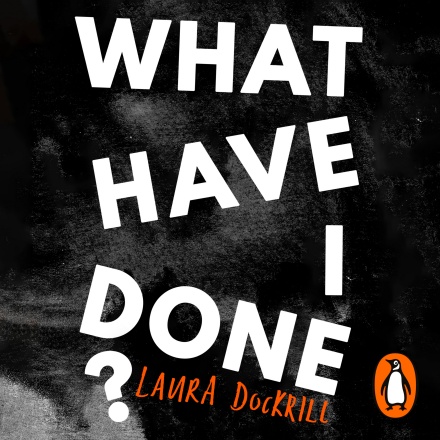
《我都幹了些什麼?》
目前,對於引發產後抑鬱的病因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但是經歷過創傷性分娩的產婦都更有可能患產後抑鬱症。多克里爾的分娩經歷非常痛苦,加上她的兒子體重太輕,需要不斷地餵食,長期的睡眠不足最終造成了她持續性的恐懼感。和凱瑟琳一樣,文化期待也給多克里爾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只不過這壓力不是來自於家庭傳統,而是來自於Instagram。凱瑟琳說,“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照片,媽媽將赤裸的嬰兒抱在懷裏,哭着笑着,十分開心。人們也總是理所應當地認爲母親就應該無條件深愛自己的孩子,這種期待讓我難以承受。”事實上,與兒子缺乏親密感所帶來的內疚時常折磨着凱瑟琳,她覺得,“(她的兒子傑特)就像是一隻親密的寵物,但我卻無法對這種親密做出迴應。什麼時候我才能開始感受到愛一般的感覺呢?”
第一個指出多克里爾可能患有產後抑鬱症的人,是歌手阿黛爾。阿黛爾是多克里爾在藝術學校學習時最好的朋友,她發現多克里爾在生完孩子之後開始變得奇怪而偏執,還會在網上搜索有關“生完孩子之後就瘋了”的內容,她對此感到越來越擔心。最後,多克里爾被送進了精神病院,那時,她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甚至懷疑她的音樂家搭檔和醫生在密謀偷走她的孩子。多克里爾在《我都幹了些什麼?》一書中對自身經歷的敘述令人感到心碎。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讀者依然能在多克里爾的文字中讀到幾分黑色幽默。
最可怕的一點是,人們往往認爲產後抑鬱只是一種性格缺陷,而不是一種心理疾病。產後抑鬱患者所面對的是一種可怕的孤獨。凱瑟琳·喬的《地獄》 和多克里爾的《我都幹了些什麼?》雖然風格不同,但是,這兩部作品都向其他身處相同境遇的產後抑鬱患者伸出了團結之手,讓她們看到了希望和出路。正如多克里爾所說,“放在很多年以前,哪個女人要是敢寫這些東西,肯定會被當成女巫或者被扔進瘋人院了。當然,也或許不會,誰知道呢?我所做的這些,也正是爲了她們!”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