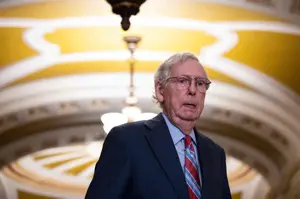今年11月11日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週年,而近日出版的由德國學者安德里亞斯·古斯基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或將帶給我們一個重新認識陀式及其作品的機會。與市面上已有的衆多陀式傳記相比,古斯基的版本不僅是新作新譯,而且不可避免的藉助其德國視角發掘出作家不爲大衆所知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那些充滿張力的畫面以及對人性的不斷拷問,也在這部新傳中清晰地呈現,揭示了陀氏作爲一位“危機”作家的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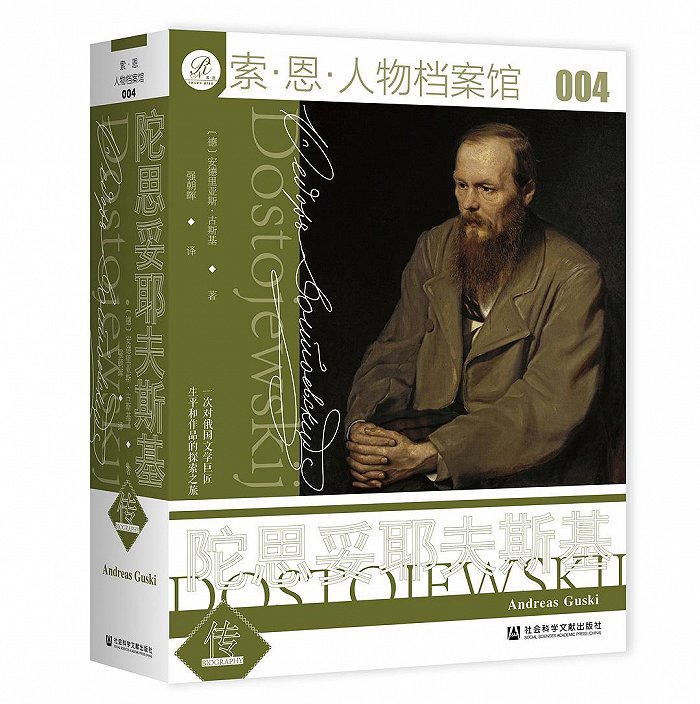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德]安德里亞斯·古斯基 著 強朝暉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1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的新書分享會上,翻譯家劉文飛與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俄羅斯文學研究室主任侯瑋紅共同探討了這部作品與俄國本土陀氏傳記的重要差異,以及我們在今天閱讀陀氏傳記與作品的意義。正如兩位嘉賓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映了俄羅斯人的民族性,他的一生都在關心人類善惡的鬥爭、自由和信仰的關係,以及俄羅斯民族的命運,而他人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分裂,都可以在古斯基的這部傳記中找到依據。
新作、新譯與新的德國視點,是古斯基版陀氏傳記的價值
在市面上衆多陀氏的傳記中,古斯基所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篇幅不算長,大約有20-30萬字,但劉文飛表示,他閱讀時卻花了更長的時間,也收穫了不少新鮮感,他將之歸納爲三個“新”。第一個“新”是指作者,無論對於劉文飛本人還是俄羅斯本土的俄國文學研究者,古斯基都是一個新鮮的名字。劉文飛還注意到,書中的序言寫於2017年11月,也就是說這是一本近年剛剛完成就被譯介到中國的作品,對於讀者而言,這意味着它涉及到的有關陀氏的信息會比以往的傳記更多。

活動現場(出版社供圖)
第二個“新”在於這部傳記是創作於21世紀的陀氏傳記。劉文飛介紹道,與其他俄國作家相比,陀氏的傳記在30、40年前並不多見,在俄語傳記中明顯少於普希金傳和托爾斯泰傳,這是因爲在整個蘇聯時期,人們對陀氏的評價不是很高,有人說他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也有人說他是反動作家。但另一方面,有關陀氏的研究著作卻很多,劉文飛認爲,之所以出現“研究多而傳記少”的奇怪現象,可能是由於傳記作家對如何評價陀氏感到爲難。
儘管如此,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前蘇聯已經出現了最早的一本陀氏傳記,作者是格羅斯曼,這本書在1987年被外國文學出版社譯介到中國。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了謝列茲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是國內學者參考較多的俄羅斯人所寫的傳記。還有一本比較重要的陀氏傳記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它創下了陀氏傳記最大篇幅的記錄。此外,較爲人知的陀氏傳記還有美國的斯拉夫學者斯洛尼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愛情》,以及陀氏夫人所寫的日記和回憶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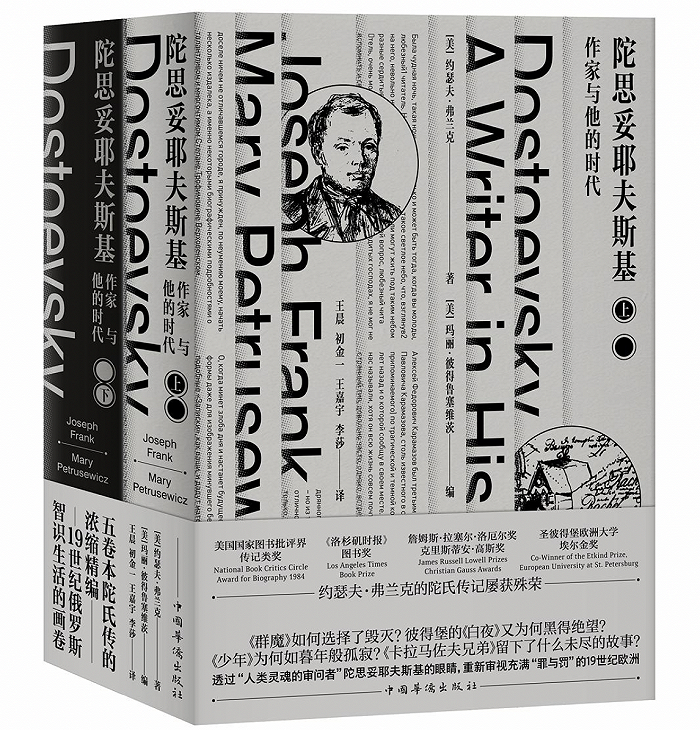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
[美]約瑟夫·弗蘭克 著 王晨 等譯
三輝·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9年
以上提到的傳記大部分都已推出中譯本,但劉文飛注意到,它們無一例外都是譯自俄語或英語,然而,古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卻是譯自德文,書中呈現出的德國視點也令劉文飛感到格外的“新”。“相對而言,它比較側重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學層面、思想史層面的理解,比如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他(陀氏)受到了很多來自康德、克爾凱郭爾、謝林等哲學家的影響。”換句話說,古斯基作爲在德語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作家,對德國哲學歷史如數家珍,對德國哲學家們的理解也會遠超別國學者,這一點是他寫作這本傳記的優勢。此外,劉文飛發現,古斯基的德國視點還表現在相對淺的生活層面,比如他會格外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外度過的那些歲月,關注他到過德國哪些地方——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陀氏的很多作品是在德累斯頓和巴黎寫成的,相當於“僑民文學”。
侯瑋紅也留意到古斯基這部傳記的新意以及當代性,她還對作家敘述的方式印象深刻。“他在敘述的時候很有電影的畫面感、時空感,很像拍攝時的搖臂,一會兒搖到陀氏的時代,一會兒搖到當代,讓你有種互相映襯的感覺。”侯瑋紅記得,在寫到陀氏去世以前不久,普希金紀念碑落成的時候,古斯基將陀氏和屠格涅夫在落成儀式上的演講說成是二者之間的決鬥。“屠格涅夫是貴族的、高傲的、帶着自信和自戀的形象,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是一個面帶病容的、神經質的、令人心生同情的中世紀僧侶的形象。”她認爲這種對細節的生動刻畫固然有演繹的部分,但作者能把演繹、想象和史料、作品以及人物等特別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確令人感到驚喜。
想要了解俄國人的民族性,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一個捷徑
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古斯基的德國視角也與俄國的本土視角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劉文飛提到,俄國人看陀氏的傳記會認爲他是一個聖人,直到現在,俄國學者包括薩拉斯金娜所寫的陀氏傳記,基本上態度都是仰視的,很少在敘述時去揣測陀氏的心理或對某些爭議性問題的看法,因爲他們認爲這是對文學聖人的解構。而在古斯基的新傳中,恰好有一章的題目叫“封聖”,其中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開創了俄國人民爲作家封聖的先例——一個作家去世以後,要擡着他的靈柩在大街上走,讓成千上萬的人爲他送葬。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都經歷了類似的送葬儀式。“作家的封聖在俄國人看來很正常,但是異域的人看,總是有點調侃和解構,何況還是在這麼新的一本書裏。西方的知識分子本來也有解構的傳統和心態,不太想把一個作家寫成聖人,”劉文飛說。
俄國內部與外部作家的另一個區別體現在他們對陀氏所代表的民族性的不同解讀。劉文飛指出,俄國人更關注陀氏身上體現的俄羅斯民族意識,而俄國境外的人是把他看作最典型的俄國人,比如他的喜怒無常、極端蠻橫,還有他的睿智,通過破解他來認識俄羅斯性。儘管都是要了解俄國人,但從這點上看兩者恰好是相反的:前者是擁戴的,後者是挑剔的。特別是在前蘇聯時期,蘇聯官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稍有貶低,這時西方會更擡舉他的現代意識;當蘇聯解體以後,蘇聯官方把他當做意識形態代表的時候,西方反倒對他有所貶低。
在陀氏誕辰200週年之際,兩位嘉賓也談到了今天人們閱讀陀氏的著作及其傳記的意義。在劉文飛看來,如果想要了解俄國的文化、文學,瞭解俄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民族性,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一個捷徑。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可能是以文學介入人的內心最深的人,因此閱讀他的作品會讓人更瞭解人的複雜性。正如古斯基在傳記中分析陀氏的小說《地下室手記》時提到,陀氏將人分成兩類,一類是知足常樂的人,也就是普通的人,另一類是“地下室人”,是懷疑一切的人。像“地下室人”面對世界的這種懷疑精神、否定精神,纔有可能幫助人在某種意義上更完滿地實現自己的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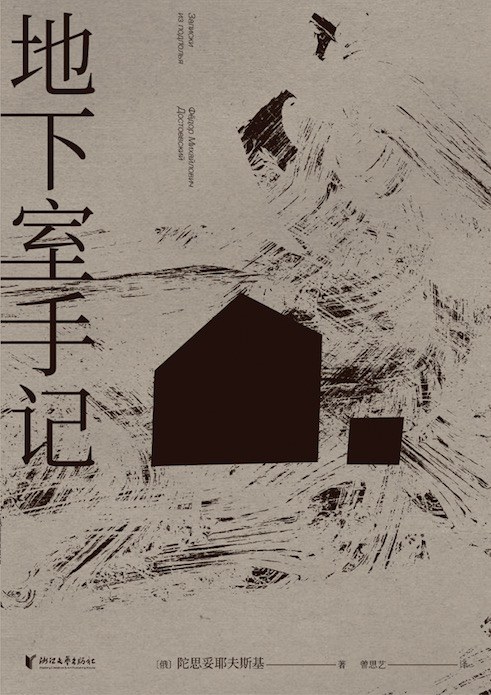
《地下室手記》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藝 譯
果麥文化 |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0-05
古斯基的傳記也格外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分裂性。熟悉陀氏的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亞的苦難歲月對於他後期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自此之後,對世俗生活的渴望和宗教意義上對新生的渴望這兩者的分裂時刻纏繞在他的思維之中。劉文飛認爲,陀氏一生都在關心人類善惡的鬥爭、自由和信仰的關係,以及俄國和歐洲的問題。他在晚年提出“俄羅斯理念”,認爲西方因爲資本主義的自私性已經失去了信仰的純潔性,只有堅守東正教傳統的俄羅斯人還在肩負一種通過改造信仰拯救世界的使命。“對於個體的人來說,他讓我們看到人本身的深刻和複雜,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他讓人看到俄羅斯這個民族的發展過程的艱難和慎重。”
侯瑋紅則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概括爲個人的、民族的/時代的,以及人類的三個方面,這三方面的本質問題是人的歸屬感,也就是肉身的安頓和心靈的安頓。在肉身上,陀氏一生都在爲健康所困擾,古斯基就提到了他所得過的疾病,包括癲癇、呼吸道疾病、頭暈、多疑、焦慮等;在心靈上,他不僅對文學事業上的成就有着各種野心和慾望,還一直對信仰持一種又想堅信又不斷懷疑的態度。“我覺得他身上反映了作爲一個人的所有矛盾的集大成,所有精神上的困頓、矛盾、求索,往大里說,就是國家的前途問題,民族的命運問題,就是人類的問題,有點像我們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劉文飛還提到,文學的寫作和閱讀從19世紀至今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人們其實更多還是在閱讀古典主義的文學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構成我們閱讀文學的一個轉折和延續,因爲小說寫作的現代性開端正是在陀氏那裏,他讓人意識到故事本身不一定重要,寫法也很重要,而且可以出現意識流,出現對生活的懷疑。侯瑋紅也認爲,陀氏的影響是滲透在當代作家的血液中的,具體到文學創作,最典型的兩個全面繼承陀氏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是馬卡寧和奧列格·帕甫洛夫。因此,無論是閱讀現代派文學還是後現代文學,讀者都可以從陀氏身上找到源頭,這也是我們在當下閱讀他的理由。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