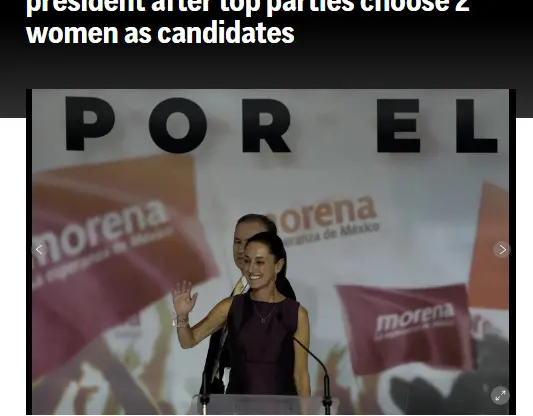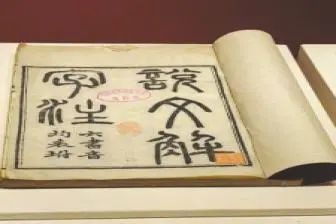文學評論家、《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羅德·布魯姆曾有一個經典的論斷,把菲利普·羅斯視爲美國當時在世的最偉大的四位小說家之一。羅斯在美國文壇的核心地位確實不可動搖,他在27歲所著的第一部小說就拿下了美國全國圖書獎,後來更是包攬了普利策獎、布克國際獎、卡夫卡文學獎等等,唯獨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但漢鬆改寫了羅斯所著的《人性的污穢》中的一段話來評價羅斯:“你還是得承認這個作家是自多斯·帕索斯以來揭露美國最透徹的人。他把一支溫度計插進了這個國家的屁眼。菲利普·羅斯的美國。”“溫度計”是在測量一個發燒的國家,正如羅斯在用文字測量美國的狂熱。
曾幾何時,美國是很多人嚮往的國度,美國夢的中產階級神話曾激勵了幾代美國人和美國移民。而今,民粹主義猖獗,冷戰思維在美國社會甚囂塵上。那麼,美國到底是什麼?美國的歷史、現在和未來,這些謎語的答案是否能到文學中尋找?日前,但漢鬆在線解讀了美國文壇神話菲利普·羅斯和他筆下美國人精神生活的病理切片,藉以一窺美國的心靈史。
大歷史下的家庭悲劇
羅斯的“美國三部曲”包含了《美國牧歌》《背叛》(又譯《我嫁給了共產黨人》)和《人性的污穢》三部小說。“三部曲”在情節上並不是一個連續有機的故事整體,但它們在主題和風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這三部作品也是羅斯由少年得志到步入花甲的一個重要變軌。1995年,羅斯與第二任妻子布魯姆離婚。兩次失敗的婚姻,加上前妻對他的辛辣指斥,使社會對羅斯的批評紛至沓來。儘管羅斯落入了情緒的低谷,卻同時步入了創作的爆發期。他以一種悲觀壓抑的筆調,用一種聚焦式的歷史思維,去回顧對他生命影響最大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
在羅斯的創作生涯中,內森·祖克曼這個角色反覆在其作品中出現。祖克曼也貫穿了“三部曲”的始終,他不僅是一個敘述者,還是一個傾聽者,是一個故事發展的催化劑。他的身份就像一個偵探,他去探尋三個主人公意識當中潛藏的祕密——有時候是通過交談,有時候是通過查證,但更多的時候是通過祖克曼自己的想象。羅斯在這個角色上投射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可以說祖克曼是羅斯的另外一個鏡像。羅斯巧妙地把他安插在小說文本當中,通過他去探尋筆下那些美國悲劇人物的內心。
但漢鬆認爲,“三部曲”採用了“家庭悲劇+大歷史”的基本結構。五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波瀾壯闊的歷史,包括杜魯門、美蘇冷戰、反越戰運動、克林頓,都在小說中作爲重要的背景出現。但同時,“三部曲”中真正的故事聚焦在一些具體而微的、平凡的美國人身上,羅斯是通過一種個人的戲劇化的失敗來折射和隱喻一個國家的歷史變軌。“‘三部曲’中有三個現代悲劇意義上的反英雄,一個是’瑞典佬’利沃夫,一個是艾拉,一個是科爾曼·西爾克。這三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載了各自時代的命運,他們不僅僅是時代的見證者,也是時代的人質,被時代所裹挾所綁架。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內心都是時代所塑造的,他們想反抗,但是最終卻無能爲力。”但漢鬆說。
《美國牧歌》:幻滅的美國夢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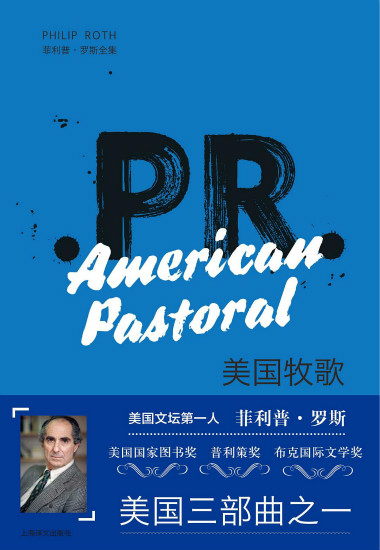
《美國牧歌》 [美]菲利普·羅斯 著 羅小云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6
《美國牧歌》中的主人公“瑞典佬”利沃夫是一個猶太人,但他憑藉自己的天賦和努力離開了猶太社區,成爲了比美國白人中產階級更像美國人的美國人。瑞典佬是典型的美國夢追逐者,能夠按照自己的人生規劃去實現野心,是一個踐行着“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手套工廠老闆。他還娶了新澤西小姐,生下一個女兒,組成了一個完美的家庭。但諷刺的是,在動盪的六十年代,他的女兒梅麗成爲了一個炸彈客、一個恐怖分子。
瑞典佬不明白,他給了梅麗牧歌般的成長環境,她怎麼會成爲恐怖分子,去放炸彈、殺人,去背叛她的家庭、背叛她的祖國,將胡志明視爲偶像。羅斯希望帶領讀者追問,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錯誤是如何鑄就的?《美國牧歌》是一部關於美國夢的小說,是一部關於失樂園的小說,是一個美國夢如何變成美國噩夢的故事。它首先是一個典型的家庭悲劇,但在家庭悲劇的背後是整個五六十年代,美國最激烈動盪的20年。正是這個時代,給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帶來了撕裂性的影響。
但漢鬆指出,美國從建國開始就不是靠血緣關係或地緣關係,或者民族國家統一等手段形成的,它是一個依靠神話構建的國家。“五月花號”就是這樣的一個神話——你只要相信美國夢,你就可以選擇成爲美國人。美國夢也就自然包含了一些美國例外論的說辭,包括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山巔之城”等等,認爲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今天的美國人則認爲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工廠。但這種美國夢式的天真正是羅斯想要解構的。越戰的故事、種族暴力的故事,其實不只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失樂園,而是整個國家的失樂園。它把二戰後洋洋自得的美國人帶進了悲慘的現實中,撕裂了美國中產階級美好生活的夢想,把發生在亞非拉國家的暴力戰爭和社會不公帶回了美國。小說中瑞典佬居住的田園牧歌式的小城,最後因爲1968年之後的種族主義暴力而成了一座廢城。
然而在但漢鬆看來,小說不僅諷刺了瑞典佬這樣一位天真的美國父親,還批判了另一個人物,那就是女兒梅麗,她代表了六十年代那些憤怒激進的美國青年。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激進化,青年們崇拜亞非拉革命,崇拜胡志明、切·格瓦拉、馬爾庫塞,但這其實構成了另外一種天真。瑞典佬的天真是相信美好的中產階級美國夢,而梅麗的天真就是希望徹底地打破美國夢,再去尋找一個公正的、普世的、完美的社會秩序。
小說中,梅麗及其同黨與瑞典佬就工廠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對於梅麗和那一代激進青年而言,工廠是《資本論》中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骯髒邪惡的場所。但是對於老一輩的美國人來說,一個世代相傳的工廠代表着一種藝術、一種誠實,是美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一種具體體現。但是那些青年過於天真浪漫,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其實是偏頗且脫離實際的。小說中的瑞典佬批評他們:“你不知道工廠是什麼,不知道製造業是什麼,不知道什麼叫資本,不知道什麼叫勞動,對什麼叫僱用、什麼叫事業,你連起碼的知識都沒有。”小說家藉此表明,滿腦子剝削、壓迫、反抗這些大詞,這樣一種理想主義其實也是危險的。
《背叛》:“每個靈魂都是製造背叛的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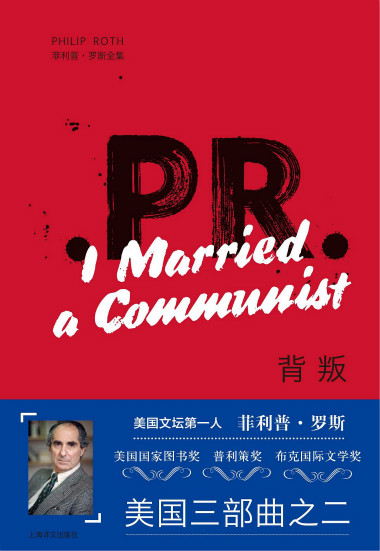
《背叛》 [美]菲利普·羅斯 著 魏立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5
作爲“美國三部曲”第二部的《背叛》在主題上與《美國牧歌》有相似之處,它講述了主人公艾拉美國夢破滅的故事。艾拉出生於普通家庭,他做過挖溝工人、侍者、礦工,接受過美共的教育,對於馬克思、列寧、恩格斯都非常的熟悉,他的身上體現了五十年代美國老左派的縮影。艾拉表面上看是一個像托馬斯·潘恩一樣的美國烏托邦的追隨者,但同時他又是一個非常膚淺的人。他年輕時以解放世界爲己任,但他後來連他的妻子他都沒法解放。隨着妻子的背叛,被污衊爲蘇聯間諜,艾拉的演員生涯告終,幻滅的不僅是他個人的美國夢,更是左派的烏托邦理想。
與《美國牧歌》聚焦於反越戰學生運動不同,《背叛》關注了於1950年代席捲美國政壇的麥卡錫主義。因而作品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告密和背叛,用書中的原文來說,“每個靈魂都是製造背叛的工廠。”羅斯的文字直指麥卡錫時代的告密文化、背叛文化,這種國家層面的政治氣候已經滲入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機理當中。很多人以愛國爲名告密,但是這種告密其實帶有着一種變態的心理需求:即使不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他也願意去害人。
但漢鬆認爲,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思想小說。借小說中祖克曼這個角色,羅斯思考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藝術的目的是什麼?藝術的追求是什麼?藝術跟現實的關係是什麼?羅斯寫道:“政治最會普遍化,而文學最會個別化。兩者的關係不僅是互逆的——還是敵對的。”他認爲,文學與政治必然是緊張的關係,因爲政治會不斷將世界簡約成一些類型、一些階級、一些屬性,但是小說家的使命是突破這些概念,是把個體當中最幽微的東西、最不可通約的東西,以最誠實的方式,戲劇化地展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是要剝奪人的自由,但文學是要救贖人的自由。
《人性的污穢》:身份政治背後的僞善

《人性的污穢》 [美]菲利普·羅斯 著 劉珠還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6
《人性的污穢》的主人公科爾曼原本是一位古典文學系的教授,他在課堂上使用“spook”(鬼魂)一詞描述兩名缺席的黑人學生,卻因“spook”還有“黑鬼”一詞而被學生冠上種族主義者的罪名,他因此憤然離職。但隨着故事的發展,作爲科爾曼朋友的作家祖克曼發現,科爾曼並非他自稱的猶太人,而是一個黑人。這對精彩的反諷烘托出了書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小說表面上描寫了美國的種族主義給人帶來的屈辱、對人的異化,但是科爾曼卻背叛了自己的種族:他既不想當黑人也不想當白人,他說“我就想當我自己”。
但漢鬆認爲,羅斯在書中非常尖銳地批判了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一種對差異的崇拜,但是在羅斯看來,不管是什麼民權運動,在這些政治正確的說辭背後,這種文化亢奮的背後,都存在着一種僞善和虛假。這種僞善和虛假讓一個人明明是黑人,卻因爲歧視黑人而墮入醜聞的深淵。羅斯認爲,所有的身份其實都是一種壓迫,所有的身份都會讓我們成爲一個“非我”。這個主題或許對美國當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反性騷擾運動以及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具有警示意義。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