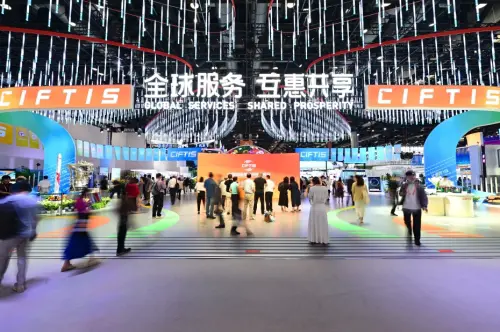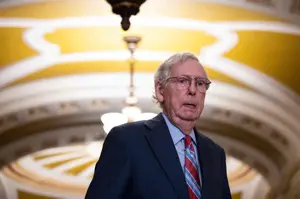亞太日報 Shannon
羅漢-阿格瓦爾今年26歲,他要到明年才能完成醫學培訓。然而,在印度最好的醫院之一的急診室裏,當病人喘着粗氣被家屬帶來時,他就是那個必須決定病人生死的醫生。
印度的醫療系統在新冠疫情的第二波殘酷浪潮中已經瀕臨崩潰。阿格瓦爾正在新德里的聖家醫院,負責着急診室的一個嚴峻的27小時夜班。
聖家醫院的每個人,無論是病人、家屬,還是工作人員,都知道沒有足夠的牀位,沒有足夠的氧氣跟呼吸機來維持每一個送到醫院門口的生命。
阿格瓦爾表示,“誰會獲救,誰無法獲救”,這該由上帝來決定。“我們不是爲了這個而生的。我們只是普通人類。但此時此刻,我被強迫做這種抉擇。”

過去兩週,印度每天單日新增病例超過30萬例,創下世界紀錄。有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是保守的。在首都,5000多張新冠重症監護室的牀位中,只有不到20張是空閒的。病人從一家醫院趕到另一家醫院,死在街上或者家裏,而氧氣則在武裝警衛下運往庫存緊缺的地方。火葬場晝夜不停地工作,每隔幾分鐘就會有遇難者的屍體運到。
路透社記錄了阿格瓦爾的馬拉松式值班情況,爲印度令人痛心的疫情,和病例激增期間醫院不堪重負的情況提供了最全面的描述。阿格瓦爾表示,他很擔心,如果自己也被感染會意味着什麼,因爲他知道自己的醫院不太可能爲他找到牀位。
阿格瓦爾沒有接種新冠疫苗。1月份正在爲醫務人員注射疫苗的時候他得病了。然後等到2月份,他開始放鬆警惕。他說:“我們都誤以爲病毒已經消失了。”
清晨的巡視
當阿格瓦爾在上午9點左右開始值班時,有四具屍體躺在一個區域,那裏本該是工作人員脫下防護設備的地方。
急診室裏的情況則更誇張。病人和親屬擠滿了每一個可利用的空間,許多人除了戴着簡單的布口罩外,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手推病牀距離很近,病人們可以互相接觸,有位病人甚至躺在庫房裏。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和護士也不再穿戴完整的防護設備。
這家醫院正處於絕望的境地 —— 通常可以容納275名成人病患,目前卻要照顧385人。醫院外貼出的告示顯示,可用的普通和重症護理病牀的數量與幾周前一樣:零。
急診室的工作通常是一項相對簡單的任務,由更初級的醫生負責,而高級顧問和專家則守護在重症監護室。但是這一規則早已被打破。現在,急診室的值班醫生纔是醫院裏最重要的醫生之一。
在開始到急診室工作之前,阿格瓦爾首先要在新冠病區的普通病房裏巡視。他和一位資深同事一起,負責65名病人。這給他的每位病患只提供了最多三到四分鐘的診療時間。
他剛查完房,就接到一個緊急電話 —— 他的一個病人發病了。他衝下樓梯,沿着燈光昏暗的走廊來到323室,那裏有一位老人已經失去了意識。
但這個病人是幸運的。他已經住進了新冠病房,與那些懇求入院的人不同,可以獲得重症監護。阿格瓦爾表示,他們雖然沒有牀位,但也不得不管。他還說,一名保安被安排在急診室外,以確保病患親屬不會試圖“通過武力”來獲取牀位。
上個月,另一家醫院的病患親屬在其死亡後用刀子襲擊了醫務人員。該市州的最高法院警告稱,如果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繼續存在,醫院可能會面臨更多法律和秩序方面的麻煩。

短暫的喘息
在德里長大的阿格瓦爾從6歲起就想成爲一名醫生 —— 這是一份在印度極具威望的工作。他在19歲時通過了考覈,並開始在首都東部一家政府醫院的附屬醫學院接受培訓,後來在由傳教士所創辦的聖家醫院當醫生。
該醫院的醫療主管和重症監護室主任蘇米特-雷表示,醫務人員們正在盡一切努力爭分奪秒。“醫生和護士們的士氣很低落,”他說,“他們知道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是沒有時間。”
無論阿格瓦爾在哪裏,當他試圖睡覺時,都會聽到心率監測器的聲音。當他在醫院裏打盹的時候能夠聽到,在自己家中的牀上也能夠聽到。這讓他無法忘記在他看顧下死亡的病人,不是因爲不夠努力,而是因爲缺乏資源。
阿格瓦爾通常在醫院裏吃午飯,但這一天, 他稱之爲“重症監護室的噪音”讓他無法忍受。他在附近的一家24小時便利店找到了喘息的機會,那裏有強勁的空調、進口麥片和店內輕聲播放的美國流行音樂。
他一邊吃着外賣咖喱飯,一邊說:“這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氣氛。我只想在醫院外休息一個小時左右,這樣我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恢復。因爲我還得在那裏待上24小時。”
急診室換班
下午3點前,阿格瓦爾回到急診室值班。親屬們圍着他,懇求他批准住院。
他的決策過程聽起來很簡單。他說:“如果一個病人發燒,那麼我知道他生病了,但他如果不需要氧氣,我就不能收他。”
“這就是標準。沒有氧氣,人們就會死在街上。所以不需要氧氣的人,即使他們生病了,我們通常也不會收留他們。”
他開始巡視急診室。他的速度很快,幾乎不看那些能夠坐起來並還有意識的病人。
當阿格瓦爾看着病人的X光片時,一位親戚問道:“他能康復嗎?”
“我會盡力的,但我不能保證什麼。”他回答道,並已經轉向下一個病人。
一位74歲的婦女卡魯納-瓦德拉正處於危急狀態。阿格瓦爾用拇指輕按她的眼窩,測試是否有反應。沒有,她的頭向前傾倒,氧氣水平低得可怕。
他告訴她的侄子普吉特,她可能隨時會死。他懇求醫生把她轉移到有重症監護室牀位的醫院。“我們家的五個人在德里的不同地方,每個人都在努力,但沒人找得到牀位” 普吉特說道,手機幾乎沒有離開過他的耳朵。
夜班
阿格瓦爾整夜都在與病房裏不斷出現的緊急情況作鬥爭。已有三位病患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輕女子。直到凌晨5點,他纔在急診室的休息間裏勉強睡了一會兒。
當他幾小時後再次出現時,瓦德拉,這位沒有在重症監護室得到牀位的老人家已經去世了。她的侄子普吉特站在一旁,看着她的屍體被裹在白色的裹屍布裏,被救護車送去火化。
在27個小時之後,阿格瓦爾的工作終於結束了,一種疲憊感讓他除了睡覺什麼都不想做。
但他還有最後一項任務 —— 一個朋友的父親生病了,他來此求助。
這是他每天都會接到的無數相似的求助電話之一。十有八九他也無能爲力,但他還是要嘗試一下。
於是他重新戴上口罩,回到診室裏。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