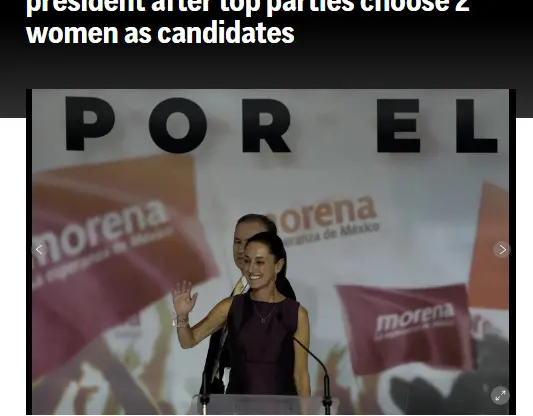瑪麗斯·孔戴(Maryse Condé)1937年生於瓜德羅普,於巴黎索邦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學術生涯成就斐然,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語文學榮休教授。她曾在幾內亞、加納和馬里居住,風靡世界的成名作《塞古家族》的靈感即來自於這段經歷。孔戴獲得了2018年的新學院獎(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亨利·路易斯·蓋茨、胡諾特·迪亞斯及羅素·班克斯等同行對其著作均有高度評價。
她的最新小說《伊萬和伊萬娜奇妙而悲慘的一生》( The Wondrous and Tragic Life of Ivan and Ivana )探討了諸如種族主義、恐怖主義和經濟不平等等課題。目前她與丈夫、譯者理查德·費爾考克斯(Richard Philcox)一同住在法國南部。
你最新一部小說的靈感來自何處?
孔戴:在我小的時候,理解世界要容易一些;現在我老了,已經完全看不懂了,於是打算把這種困難寫出來。當你成了一名老作家,你就會成天想着自己——你的父母和童年。我決定藉由雙胞胎伊萬和伊萬娜,講述一個和當今而非昨天的世界有關的故事。另一方面的靈感來自克拉利莎·讓-菲利普被殺一案,這名青年警官出身於馬提尼克島,在巴黎查理週刊襲擊事件中被來自馬裏的恐怖分子阿米迪·古力巴里殺害。一名黑人男性竟然能殺死一名黑人女性,這讓我萬分沮喪,如此一來塞澤爾的黑人性理論(theory of négritude)就毫無意義了——它曾宣稱所有黑人都是兄弟姐妹。
你以前說過:“我不會去寫毫無政治意義的事情。”對於眼下這個全球反種族主義抗議風起雲涌的政治時刻,你有何看法?你是否感到變革即將來臨?
孔戴: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相信形勢會有改善,但仍然需要一些時間。法國也有一些人在抱怨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的暴力。運動不止發生在美國,它已經席捲全世界。法國花了漫長的時間纔將奴隸制確認爲反人類罪。在18世紀,一些科學家還支持奴隸制,宣稱黑人更下等、更接近於動物,我們依舊在對抗這種誤解。這並非易事,我們終將取勝,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在各方面都稱得上是樂觀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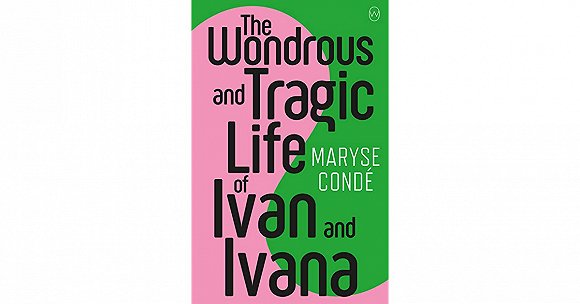
《伊萬和伊萬娜奇妙而悲慘的一生》
請談一談你早年的活動經歷……
孔戴:我從小受的教育來自父母,他們對法國抱有信心,深信法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父親經常告訴我:“啊,法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但如今我理解了某些他們不願直面的東西——我們從來沒談過奴隸制或殖民主義。我決定要好好了解一番這些在我面前被隱瞞起來的課題。年紀輕輕很難有什麼自己的見解以及自由的思想,你必須年齡大一點、足夠強大以及更加成熟,才能去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你曾提到,你在年近四十之前一直沒有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說《赫爾馬克霍恩》( Hérémakhonon ),原因在於“不夠自信,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給外部世界”。
孔戴:小時候父母對我幾乎是溺愛。我對外部世界全無察覺。我堅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屬於最聰明的那一撥人,但我到法國學習之後就發現了人們的偏見。人們只憑我是黑人就認爲我更下等。我必須向他們證明自己的天分,向每個人展示我的膚色是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頭腦和心靈。
你人生中的轉折點是什麼?
孔戴: 我在巴黎的費奈隆公立高中讀書時結交了一個女孩,她的父親讓·布魯哈特持共產主義立場,在索邦大學教授歷史,他教導我要對自己有自信。他還讓我明白瞭如何用一個被殖民者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瓜德羅普的設立源自於法國獲取殖民利潤的企圖,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是如何遭到滅絕的。
你幼時的閱讀習慣如何?
孔戴:我讀《呼嘯山莊》時大約10到12歲,母親的一位朋友知道我愛好閱讀,於是送了我這本書。我之前從來沒聽說過艾米莉·勃朗特,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書能夠貼近我的內心——它彰顯了文學的力量,你雖然是一名英國作家,但卻能抵達一名加勒比兒童的內心。瓜德羅普有一處破敗之地,廢棄的糖廠和種植園建築和《呼嘯山莊》以及約克郡沼澤的景緻很接近。當我告訴母親的朋友自己是如何熱愛這本書並且想成爲作家時,對方回答說,像你這樣的人不會從事寫作。她指的究竟是黑人、女性還是小島上的人?我永遠也無法知道。
哪些作家曾經爲你帶來過靈感?
孔戴:我非常喜歡瑪格麗特·杜拉斯,也喜歡西蒙尼·德·波伏娃、讓-保羅·薩特、米歇爾·福柯、薇奧萊特·勒杜和路易·阿拉貢。
你的枕邊書有些什麼?
孔戴:我現在聽有聲書,最近比較喜歡愛德華·路易、蕾拉·斯利馬尼和愛麗絲·澤尼特爾。
你的寫作日程一般怎樣安排?
孔戴:我視力太差了,目前都口述給朋友。我會在腦子裏想好一切然後口述。當我的朋友把章節讀給我聽時,我就能修改我不喜歡的部分。寫作對我來說就像一股難以抗拒的力量。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