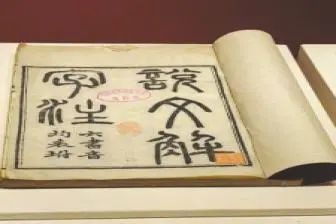1993年,我從澳大利亞的一座大都市移民到了蘇格蘭高地上一個破敗的農場,從繁華而多元的世界落入了與世隔絕的寧靜之中,文化衝擊讓我覺得自己彷彿來到了另一個星球。英國社會的許多方面都讓我感到壓抑,雖然這份壓抑沒什麼必要,但我還是很壓抑。我與生俱來的疏離感日益加深,身體也變得很不舒服。我在一所護理中心工作,但我得從農場騎15英里的自行車通勤,遇上惡劣天氣我不敢騎車的時候,就搭乘出租車上下班,本就微薄的工資幾乎花了個精光。最後,妻子建議我專心寫作。
我一直想着要寫一部小說,講述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綁架了一隻小猴子,把它的毛剃掉,花錢給它做手術變成人,然後把它作爲他們的孩子領入社會。我希望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向人們講述差異,講述我們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願意接納甚至容忍差異。但我越是琢磨,就越是明白,這部小說將會成爲一部諷刺小說,但我不想寫諷刺小說。我想寫一本震撼人心的書,一本讓人永遠無法忘懷的書。

2013年同名改編電影《皮囊之下》裏的斯嘉麗·約翰遜 圖片來源:Allstar/FILM4/Sportsphoto Ltd./Allstar
我在高地上的居所有一種奇蹟般的美麗。我會伴着成羣的牛羊、沿着史前的海岸漫步,大自然的奇異之美讓我驚歎,可對焦慮與悲傷的感知卻沒有絲毫消散。慢慢地,另一種手術改造生物闖進了我的腦海——伊瑟莉,爲了“以人類的身份”在地球上活動,她經歷了殘忍的改造,受僱做着可以想象到的最惡劣的工作。她的故事會帶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如何對待被我們視作“他者”的人、事與物。這個故事還隱含了戰爭和種族主義的問題,它看到了工業化養殖的恐怖,看到了那些迷失的、不被愛的人的脆弱,他們被推到羣體的邊緣,在那裏,掠奪者可以隨時把他們帶走,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和關心。
我以前寫過不少書,都收進了抽屜裏。其中一本《絳紅與雪白的花瓣》終於讓我還清了房貸,享受到了極少數嚴肅文學作者所獲得的名聲。但《皮囊之下》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它徹底改善了我的生活。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負擔,相反,我可以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些有趣的機遇。

《皮囊之下》 [英]米歇爾·法柏 著 楊蓓 譯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16-10
這些年在文學節上,不少《皮囊之下》的粉絲都來感謝我讓他們變成了素食主義者。我不知道該怎麼接這種話,我自己都不是素食者。對我來說,《皮囊之下》並不是在講述吃肉的罪惡,而是在講述我們在做完決定後逃避道德責任的罪惡。然而,這部小說有它自己的力量,它可以適應不同讀者的需求,對於那些重要的問題,它也會給出不同的解答。這也一直是我所有作品的創作宗旨。
《皮囊之下》並不是一本暢銷書。雖然它的口碑不錯,但在英國的銷量不溫不火,在美國更是賣得一塌糊塗。不過它給大衆留下了印象,不斷有新的讀者會找來看。伊瑟莉也仍開着她那輛拍得嘎吱作響的豐田車,四處去尋找新的獵物。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