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人,事情總會對我產生影響。密切關注周圍發生的事情是我生存的一種手段: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需要這樣做,我需要把我的所見所聞寫下來。我夜以繼日地練習觀察,發展出了已故作家納丁·戈迪默所說的所有作家都有的“超乎尋常的觀察力”,甚至可以變成“一種可怕的疏離”。這並沒有讓我受歡迎。一位朋友對我說,“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忍受一直這麼警覺。”另一個說,“我不想成爲你所看的東西的一部分。”第三個說,“你那可怕的眼睛一直在觀察。”
不過,在性情和經濟需要的驅使下,我還是找到了這個習慣的用武之地,並設法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可以謀生的作家。
步入中年的我,在一天上午晃進了一個法庭,我坐下來,全神貫注地聽。一天的時間在5分鐘內就過去了。我迷迷糊糊出現在大街上,我很感動,深知這就是我一生一直在無知地練習的東西。一個新的世界裂開,我徑直走了進去。我靜靜地坐着。我看,我聽,我寫,我想,“我生來就是爲了這個。”
但現在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用來集中注意力、用來鍛鍊我唯一的技能的設備,已經開始磨損。一兩年前,漸漸地,我發現越來越難聽到人們在法庭上說的話。我慌了——我是不是要放棄工作了?我去做了一個測試,年輕的聽力學家說,這種聽力損失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是正常的。正常?難道我們都是帶着沮喪和焦慮的心情到處走動嗎?
他把我帶到一個後面的房間,給我看了一排在桌子上擺成一條曲線的助聽器。一邊是老式的那種看起來像一包粉色泡泡糖的助聽器,另一邊是一個微小的、沒有重量的鐵絲和一種不配稱之爲金屬物質的裝置。
我說:“我的一個朋友剛買了助聽器。他花了一萬塊錢。我希望我支付的費用比這少得多。”“他的聽力損失有多嚴重?”“他告訴我,在他戴上助聽器之前,他已經忘記了鳥兒會唱歌。”“哦,”聽力學家說,“你大概需要花一半的錢。”
我花了五千塊錢買了一個帶音量按鈕的精緻小鉤子,把它們塞進耳朵裏,然後匆匆離開。天啊,斯旺斯頓大街上的車流聲! 有軌電車的鳴叫!我又可以和我的孫子們一起看《神煩警探》(Brooklyn 99),幾乎可以跟上這部劇快速的對話節奏,雖然他們的笑聲還是比我多一倍。我只能完全聽得懂莊嚴的、句法複雜的霍爾特警監:這是我對他產生巨大迷戀的另一個原因。

《神煩警探》劇照,霍爾特(右)與戀人凱文
但在法庭上我還是聽不見。意志力和聽力學家的藝術無法戰勝那些建築中無望的聲音系統,無論是高大的維多利亞式大廳,還是現代休息室般的空間,都被笨重的紅木所堵塞,悶悶的聲音耷拉着,消失在地毯中。
在我放棄並悲壯地蹣跚回家的那天,我瞥見最高法院的外門上貼着牌子。那是一張“對1、2、3、4、6、8、9、10、11、12、13、15號法庭進行聲學處理工程”的文物許可證。
太晚了,我已經放棄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爲什麼能如此準確地引用那個牌子上寫的字,那是因爲我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這就是作家注意事情的方式:你發現了你無法想象有任何用處的細節,你把它們記錄下來。當時間追趕上來,你正在寫的東西中出現了一點空隙,它們就會從黑暗中跳出來,新鮮而閃亮。你抓住它們,把它們擦亮,然後塞進你的作品。
大家都告訴我,我們這一代人都在做白內障手術。和助聽器一樣,它的價格貴得讓人唏噓不已。但我已經有一段時間看什麼都覺得暗淡無光,毫無特色,所以我就去做了。當我跟一個醫生朋友提起這筆費用時,她說:“呵呵,你的錢都夠給一整個馬場的人做白內障手術了。”但相信我,我很感激不用看到浮游物像蟲翼一樣飄過我的視野。再次享受色彩、質感和距離的盛宴讓人興奮不已,即使我的眼睛恢復得比廣告上說的要慢得多,其中一隻眼睛還半閉了好幾個月,以至於在我下一本書的宣傳照中,我看起來又笨又陰險,就像一個年邁的海盜。
然後是大火之夏。然後是新冠病毒。一切都放緩,停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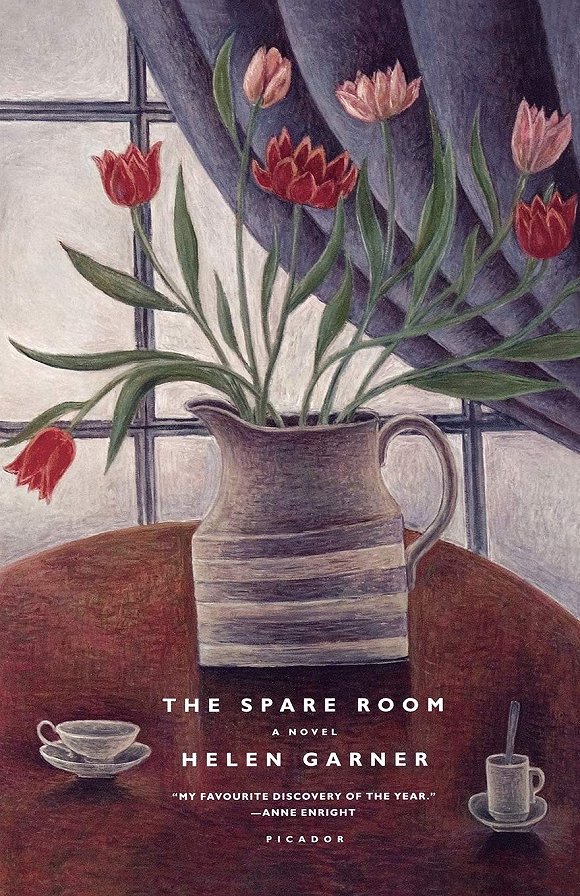
《空餘的房間》
我是幸運的。我有工作要做:將我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第二卷日記剪裁歸檔出版。隔離期間,我不能跨城到平時藏身的出租辦公室去。於是我走進家中的房間,並關上了門。
就像我安靜的屋外世界一樣,時間把自己裏外顛倒。40年的日常工作習慣灰飛煙滅,新的習慣從灰燼中萌生。我沒有早睡,也沒有吃完早飯就直接開始工作,而是在沙發上一直沉浸到凌晨一點,津津有味地欣賞着野性十足的猶太人單口喜劇和女偵探的舊案調查。我八點醒來,讓家丁出去,快走40分鐘,在墊子上做普拉提,然後整理郵件。到了中午,我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在一摞舊筆記本的包圍下,我會一直工作7個小時。我從不疲倦,從不需要小睡,餓了才吃,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我犯關節炎的部位——手腕、腰部、左腳——一點都不疼。我一直在想,是因爲我很快樂嗎?窗外的世界正在一發不可收拾地走向地獄,我這個年齡的女人還有資格快樂嗎?
我開始疑惑,爲什麼和“關注(attention)”搭配的動詞是“付出(pay)”?關注是一種債務?一種責任?一種稅收?還是一種精力的付出?這句短語中似乎涉及到了工作,或者說是犧牲。如果我們付出了,又能換回什麼呢?
當我翻閱筆記本時,我簡直不敢相信,30年前我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有多麼渺小。我的天,我簡直是注意力的女王!我花1.19澳元買了兩塊排骨。我熨燙桌布。一個從未聽過多利·帕頓的歌的成年男子。一個修女說她的臉色“和這些胡蘿蔔一樣紅”。我朋友的金鞋。一些聞起來像蘑菇的花園泥土。一個煮熟的雞蛋。一把3B鉛筆。一根夾在醫生頭髮上的聖誕裝飾品碎片。當我再次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它們顯得太珍貴了,像是具有意義的小炸彈。雖然當我把它們寫下來的時候,我認爲它們不過是一段段敘事之間的碎片和片段,是我每天用來練習的原材料。
我唯一能提供給這個世界的就是我的注意力。有時在凌晨兩點,我覺得這不算多,遠遠不夠,幾乎不算什麼。但現在,重讀我關注和隨機保存的記錄,我開始發現,我做的比我知道的要多。我想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