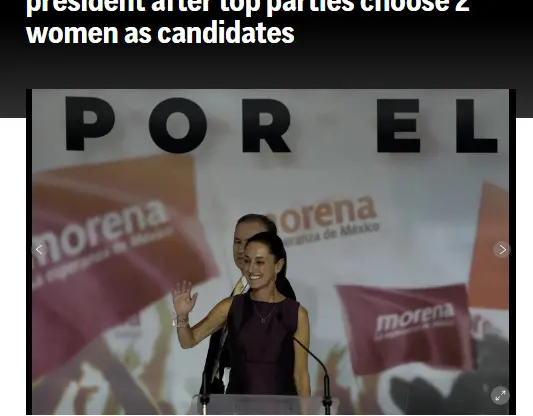亞太日報 Shannon
醫學院學生恩雅-埃格伯在課上解刨屍體時,哭着逃離了教室 —— 這並不是年輕人感到恐懼時應該有的反應。
這位26歲的年輕人仍然清楚地記得,七年前,在尼日利亞卡拉巴爾大學的那個星期四的下午。他和同學們一起圍着三張桌子,每張桌子上都擺着一具屍體。幾分鐘後,他尖叫着逃離。
他的小組準備解剖的,是他朋友迪文的屍體。“我們曾經一起去俱樂部,”他說,“他的右胸上有兩個彈孔。”
奧伊弗-安娜追着埃格伯跑出教室,發現他正在外面哭泣。“我們在學校使用的大多數屍體上都有彈孔。當我意識到這些人可能不是真正的罪犯時,我感到非常難過,”安娜說道。她補充說,有一天清晨,她在醫學院停屍房外看到了一輛滿載血腥屍體的警車。
埃格伯給迪文的家人發了一條信息 —— 迪文和三個朋友外出,在回家的路上被安全人員逮捕。此後,家人們一直在不同的警察局找他。可最終找到的,是他的屍體。
埃格伯的驚人發現凸顯了尼日利亞缺乏可供醫學生使用的屍體這一事實,以及被警察使用暴力的受害者可能面對的情況。
在16至19世紀,將被處決的罪犯屍體交給醫學院 —— 這種懲罰也促進了科學事業的發展。
根據2011年醫學雜誌《臨牀解剖學》的調查,尼日利亞醫學院使用的屍體中,90%以上是“被槍殺的罪犯”。在現實中,這意味着屍體是來自被安全部隊槍殺的嫌疑人。他們的年齡在20到40歲之間,95%是男性,其中四分之三來自社會地位較低的階層。

“救護車任務”
去年,尼日利亞政府在各州設立了司法調查小組,以調查關於警察暴行的指控。這是對“EndSars”抗議活動的迴應,該抗議活動是由警方特別反搶劫小組(Sars)射殺一名年輕人的視頻所引發的。
許多證人稱,他們的親屬被安全部隊逮捕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在大多數情況下,警方爲自己辯護稱,那些失蹤的人是在交火中被打死的武裝匪徒。警方發言人弗蘭克-姆巴也表示,他不知道有任何警方將屍體扔到解剖實驗室或停屍房的案例。
但在提交給司法小組的書面證詞中,36歲的商人切塔-納馬尼稱,他在2009年被關押的四個月中,曾協助過安全人員處理那些被他們折磨或處決的囚犯屍體。
他稱,有一晚,他被要求將三具屍體裝進一輛貨車,這項任務在拘留所裏被稱爲 “救護車任務”。然後警察把他鎖在車裏,開車到附近的尼日利亞大學教學醫院,然後他在那裏卸下了這些屍體 —— 他們被一名停屍房的工作人員帶走了。
在東南部城鎮奧韋裏,私營的阿拉丁馬醫院太平間不再接收罪犯的屍體,因爲警方很少提供死者的身份證明或通知死者的親屬。停屍房管理員烏貢納-阿馬西說:“有時,警察試圖強行要求我們接收屍體,但我們堅持要求他們把屍體送到政府醫院。”
他補充說:“私人停屍房無權向醫學院捐贈屍體,但政府停屍房可以。”
在尼日利亞,有一項法律規定可將政府停屍房中“無人認領的屍體”交給醫學院。
親屬們被矇在鼓裏
一位資深律師弗雷德-奧努奧比亞解釋稱,親屬有權領取合法處決的罪犯的屍體。“如果在一定的時間內沒有人認領,屍體就會被送到醫學院。”但他表示,法外處決的情況更糟,因爲親屬永遠無法收到死亡通知,或者無法找到屍體。
埃格伯的朋友、迪文的家人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才能夠給他一個體面的安葬。
至於埃格伯,在看到他朋友的屍體後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創傷,以至於他一度放棄了自己的學業。他最終比自己的同學們晚畢業一年,如今在一家醫院的實驗室工作。
迪文的家人設法讓參與殺害他的警官被解僱 —— 雖然正義感不強,但仍比許多其他尼日利亞人所經歷的要好些。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