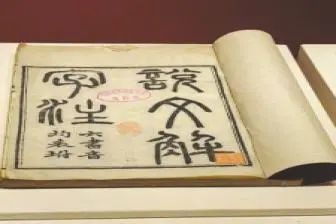據《紐約時報》報道,當地時間2月3日,90歲的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英國劍橋的家中去世。
出生於富庶猶太家庭,以德語、法語、英語爲母語,文學批評家、翻譯理論家斯坦納自稱“中歐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文化和歐洲文學語言如數家珍,會多門語言,博覽羣書。他主要研究的領域涉及語言、文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猶太人大屠殺的影響。英國小說家拜厄特(A.S.Byatt)曾把他描述爲“一位來得太晚的文藝復興巨人……一位歐洲玄學家,卻有着瞭解我們時代主流思想的直覺”。
在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大背景之下,1944年,斯坦納到了紐約,成爲了美國公民,他一面反思大屠殺,一面觀察現代生活中語言的退化,並以此爲基礎在1967年完成了代表作《語言與沉默》。身爲“中歐人文主義者”的斯坦納在納粹軍官身上看到,一個人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讀歌德和里爾克,卻不妨礙他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爲什麼會這樣?他追問,文學和知識究竟應該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斯坦納看到,語言是文化的代表。現代西方政治上的非人道(尤其是納粹),夥同隨之而來的技術化大社會,使得大衆教育教出了“一種特殊的半文盲,只在非常有限和充滿功利的範圍內閱讀和理解”,導致了語言文化的濫用與污染,使西方文學的創作陷入自殺性修辭“沉默”。
爲《語言與沉默》作序的學者李歐梵認爲,斯坦納在書中展現出了“縱橫四海”的批評方法。斯坦納指出,作爲一個有知識的文學批評家,勢必非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讀西方的經典著作,與文盲相差無幾,而侷限於一國的文學,也是井底觀天。所以他批評他的老師——牛津大學的名批評家利維斯(F.R.Leavis),說他只論英國文學,專捧勞倫斯(D.H.Lawrence),但是如果把勞倫斯的作品與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則顯然是小巫見大巫,所以他最恨文學上的褊狹。

《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 [美] 喬治·斯坦納 著 李小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和2019年去世的哈羅德·布魯姆一樣,斯坦納不是結構主義或精神分析這類“理論家”。他認爲,理論是人類失去感知耐心的墮落表現,不僅簡化了語詞的豐富性,還剝奪了文學鑑賞和闡釋功能的獨特尊嚴。他說,理論在文學、歷史、社會學等論述上的勝利,其實是自我欺騙,是因爲科學佔據上風,人文學科爲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
在《語言與沉默》當中,斯坦納一直關注人文素養(humane literacy)這個概念。他指出,在閱讀中,讀者不是被動的角色,批評家對於同時代的藝術有特殊的責任。批評家“不但必須追問,是否代表了技巧的進步或昇華,是否使風格更加繁複,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時代的痛處;還需要追問,對於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時代藝術的貢獻在哪裏,或者它帶來的耗損在哪裏。作品主張怎樣用什麼尺度來衡量人?”李歐梵稱,“在此書中,他處處反思歐洲文化經歷納粹浩劫後的反響,令我深深感動。我再三咀嚼此書中的篇章,甚至學習斯坦納的英文文體。”在文學評論中,斯坦納正是這樣顯示出“憑藉風格之力,批評也可能成爲文學”。

喬治·斯坦納
在文學批評領域,斯坦納讓人們看到,一個真正的文學批評家不是二傳手,而是進行再創作。在翻譯研究領域,斯坦納也強調譯者的主體性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當中,譯者逐漸從邊緣地位上升到文化傳播者和歷史參與者的中心地位。斯坦納1975年的著作《通天塔之後:語言與翻譯面面觀》提出的闡釋學有關理論成爲了研究譯者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的視角。在本書中,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譯”的判斷,並且指出以闡釋學爲基礎的翻譯四步驟:信任、侵入、吸收和補償。信任,就是譯者相信在原文本中一定有能夠可以理解的意義。侵入,則反映在譯者的理解上,因爲譯者“無法不對他的時代和背景妥協”,而譯者的侵入也可以讓原作在譯入語當中獲得第二生命。吸收是譯者侵入的目的和結果,譯者應該引進並消化原文的核心信息。但譯文必然會改變乃至重置原文的結構,在侵入和吸收之後,損失無可避免。因此第四步補償,就是達成原作和譯作之間的平衡。這四個步驟無不與譯者的主體性相連,在“茶杯、麥克風、譯員”成爲主流,譯者常常拿來與機器翻譯進行比較的今天,翻譯家也不斷地引用斯坦納,來爲自己存在的價值辯護。
隨着哈羅德·布魯姆、喬治·斯坦納等當代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相繼離開,我們或許正在迎來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