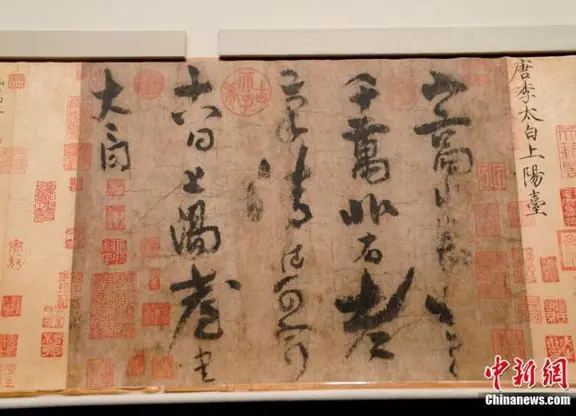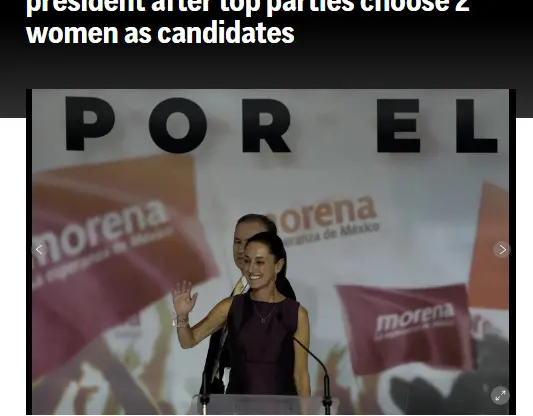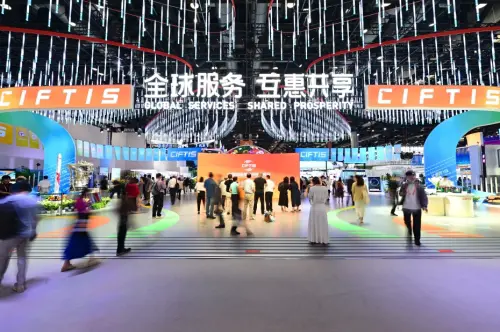亞太日報 Shannon
2018年1月的一個週六的晚上,納迪亞-瓦萊裏在倫敦西部參加了一位即將結婚的朋友的聚會,當時她失去了一個小時的記憶。
據她回憶稱,在倫敦東部的一個乒乓球場點了一杯朗姆酒後,她與新郎和他的朋友一起打乒乓球,再後來的一切都是空白的。“我當時完全昏了過去,”瓦萊裏說,“我的生命中大約有一個小時是沒有人能夠說明的。”
當37歲的瓦萊裏恢復知覺時,她已經癱倒在酒吧前的一張桌子上。她後來發現自己的大腿內側有淤青,腹股溝處的疼痛一直延伸到脊柱。“我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斷斷續續地說。
她說話小心翼翼,試圖在抑制過去三年來破壞她生活的憤怒。她決定放棄作爲性侵犯倖存者的匿名身份,分享她的故事,並強調,倫敦警察局沒有調查她的案件。
瓦萊裏的經歷聽起來像是一個關於如何不調查性侵犯案件的教程 。“這種情況一直在發生,”她的律師德爾蒙特表示,“以這種方式對待受害者是非常典型的做法。”
在她被襲擊的第二天,瓦萊裏就報了警。即使在今天,當她解釋男警官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時,她仍然感到難以置信:每年的這個時候,他們總是看到此類的案件增加。
她說:“他們甚至沒有問我發生了什麼,也沒有告訴我要去做檢查。什麼都沒有。”
調查變得越來越糟糕。在沒有警方介入進行法醫檢查的情況下,瓦萊裏與她的家庭醫生預約了尿液檢測。她被送到醫院進行藥檢血液測試,但這並不能確定藥物中的所有化學成分。

次日,星期二,瓦萊裏再次報警,警方派出了兩名女警官到她家,花了七個小時訊問她,提取了棉籤和尿液樣本,並收集她那晚所穿的衣服。
他們爲瓦萊裏指派了一名受過性犯罪調查(SOIT)培訓的官員。“她本應到我家來,但她卻只是打了電話,”瓦萊裏說,“她問我的第一件事是我穿着什麼?我準備好讓人拿走我的手機了嗎?我是否準備好了與陪審團辯論,以證明這發生在我身上?”
瓦萊裏感到惶恐,覺得自己無法呼吸。當她恢復平靜後,她在家中對這名官員說:“我不認爲,對受害者的羞辱和指責是我想聽到的第一件事,因爲這已經是犯罪發生後的好幾天了。”
“從倫敦警察局聽到這句話真是令人厭惡,尤其是這個部門是專門爲強姦、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設立的。”
晚上11點,瓦萊裏在沒有警察護送的情況下被安排去了性侵犯參考中心“The Havens”。她進行了5個小時的侵入性測試,但警方並未將樣本送去做毒理學報告。
此外,警方最初告訴瓦萊裏,他們並沒有得到酒吧裏有關於她的閉路電視錄像。他們多次被告知,授權管理錄像的經理不在,他們必須再來。最後,警察在酒吧留下了一個USB硬盤,並要求經理將錄像存入其中。
“(酒吧稱)當他們試圖下載時,那段時間的錄像被隨機刪除了,”德爾蒙特說,“警方無法查出它是如何被刪除的。”
“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我永遠不會知道我身上發生了什麼,”瓦萊裏說,“我想說很多髒話,因爲他說得好像他不在乎。他似乎並不明白其中的嚴重性和影響。”瓦萊裏認爲警方從未想過要繼續調查。她認爲:“他們試圖讓我放棄整件事情。”
律師德爾蒙特表示:“沒有人說調查性暴力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你必須積極主動地支持受害者,可是他們並沒有。根據我的經驗,這很普遍。有些機構不願意追究這類案件。”
“由於警方的失敗和缺乏積極主動的調查,瓦萊裏永遠不會知道是誰襲擊了她,”德爾蒙特補充道,“在她被襲擊前能接觸到其飲料的人,既沒有被確認,也沒有被詢問。”
瓦萊裏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不斷敦促倫敦警察局查清她的遭遇,但在2019年2月14日,他們宣佈不會再採取進一步行動。瓦萊裏通過婦女正義中心聯繫了HJA,並決定提起訴訟。“我意識到,我必須爲自己的正義而戰,”她說,“倫敦警察局的每一步都辜負了我。”
2020年9月,倫敦警察局與瓦萊裏的民事訴訟案達成庭外和解,並向她支付了3.5萬英鎊的賠償。但市政廳不承認任何責任,並拒絕了寫道歉信的要求。不過他們表示將從瓦萊裏的案件中吸取教訓,並將其用於培訓。瓦萊裏則表示:“我並不覺得我贏得了什麼。”
因犯罪而受傷的受害者通常可以向刑事傷害賠償局(CICA)求助。但德爾蒙特表示:“由於警方的失誤,瓦萊裏甚至很難向CICA證明她是犯罪的受害者。因此,不幸的是,她在獲得進一步賠償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困難。”
瓦萊裏在被襲擊前非常有活力,但這次襲擊給她留下了脊柱神經損傷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兩年來,她一直依靠柺杖行走,並需要持續對根部神經注射。她由於精神和身體健康問題一直在接受治療。
“我每天都會想起它,”瓦萊裏說,“它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我想知道我是否還能正常走路。我無法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只能打車出行。受到如此嚴重的人身攻擊,而且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瓦萊裏斷斷續續地補充着:“它還毀了我的婚姻。”淚水順着她的臉頰流下。
她在1月份與丈夫分居,並搬出了她們的家。在此之前,她不得不重新尋找住所,還有支付醫療費用。“就收入而言,當時(遇襲前)我正處於事業的高峯期,”她說,“現在我的工作大量地減少,薪酬也降低了。”
她會再去找警察嗎?“不可能,”她說道“我不會再對自己這樣做,我也不希望別人這樣做。”
瓦萊裏認爲,警方今後應該培訓更多專業的女警官。她希望自己的出發點是支持受害者和創見一個案件,而不是從一開始就試圖破壞它。
瓦萊里正在將她的生活重新整合起來,她說:“我性格中的一件事沒有改變:你不會讓我保持沉默。我只能希望,這可以產生一些影響。”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