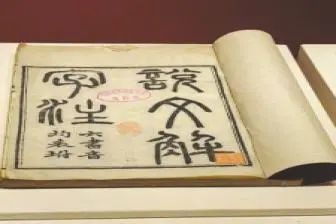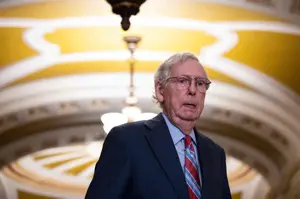照顧一個人意味着什麼?
當越來越多的人試圖照顧被隔離的父母,得知有人在醫院裏沒有親人的情況下死去而心疼不已時,這個問題就在無數人的腦海中浮現。
“照顧一個人”有一個公認的含義。但在一些奇特的情況之下,它通常的意思會被顛覆。比如,從暴徒的口中說出同樣的短語——“我想讓你照顧某人”,可能意味着謀殺。即使是在不那麼險惡的情況下,簡簡單單一句話的含義也可能被深深顛覆。
在我們度過當前危機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重讀了兩部小說——J.M.庫切的《恥》和阿爾伯特·加繆的《鼠疫》——之後。
人們在想到1999年獲得布克獎的《恥》時,往往會想起一位南非的大學教授在與他的學生髮生短暫而令人作嘔的風流韻事後被曝光的故事。當我在一月份決定重讀這部小說時,我想知道,根據最近的“取關文化”( 一些明星或名人往往因一句話或一個行爲而遭遇網友的“取關”甚至抵制——譯註 )和反性騷擾運動的發展,《恥》讀起來是否會有所不同。
在庫切的小說中,主人公大衛·魯裏是一位英語教授,當他的不良行爲公之於衆,他事實上在社會和職業上都遭到了驅逐。因爲覺得自己與衆不同,他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式贖罪,但他丟掉了工作,離開了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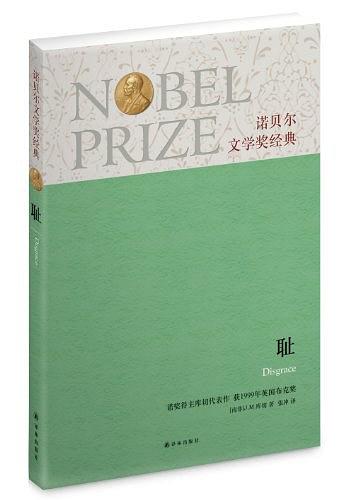
《恥》 [南非]J·M·庫切 著張衝 譯 譯林出版社 2013-2
但所有這些只是一個序曲。魯裏去農場和他成年的女兒住在一起。在那裏,他在一次入室行竊中被襲擊,並被鎖在一個房間裏,而他的女兒在房子的另一個房間被強姦。在此之後,全書的情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如果《恥》一開始是關於當男人濫用權力時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的故事,那麼它逐漸變成了另一種“恥”——在極端情況下,我們無法相互照顧的“恥辱”。
讀完《恥》後,我像過去一兩個月裏的許多人一樣,把目光轉向了《鼠疫》,並驚訝地意識到這兩本書在許多方面存在相似性。
加繆這部偉大的小說主要講述了在阿爾及利亞城市奧蘭爆發瘟疫期間醫生裏厄的故事。這本書經常被認爲是一部法西斯主義的延伸寓言。但在全球流行病大爆發期間,它卻被更多人當成了直接的報告文學來解讀。
醫生應該照顧他們的病人,拯救生命。但在瘟疫期間,裏厄難以拯救任何人——在被隔離的小鎮上,醫生的家庭訪問“變得難以忍受”。“診斷出感染意味着需要迅速移走病人。這時開始出現困難、變得抽象,因爲家人知道,除非病人被治癒或死亡,否則他們再也無見到他。”
就像如今的醫務工作者一樣,裏厄必須服從抽象的要求:將傷害降至最低。讓傷害最小化優先於更多其他的人類衝動:觸摸、情感、憐憫和同情。傷害最小化不僅優先於對“照顧”意義的一般理解,也優先於人類的“權利”觀念。
事實證明,我們沒有權利。這只不過是一種光榮的虛構。更爲迫切的抽象概念,例如打敗瘟疫,或者用今天的說法,“拉平曲線”,充其量讓人們擁有了臨時性的權利。
裏厄當然會感到憐憫。他當然認爲人們死時要有親人的陪伴,應該有尊嚴地安葬。但在瘟疫的緊急時刻,憐憫又有什麼用呢?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現在全世界的醫務工作者發現自己正陷入類似的境地。在《華盛頓郵報》日前的一則視頻報道中,布魯克林麥蒙尼德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生莫妮卡·蓋坦說,她專門研究傳染病,“是爲了讓人們變得更好”時,聽起來幾乎有些羞愧,她只能承認“我們能提供的東西很少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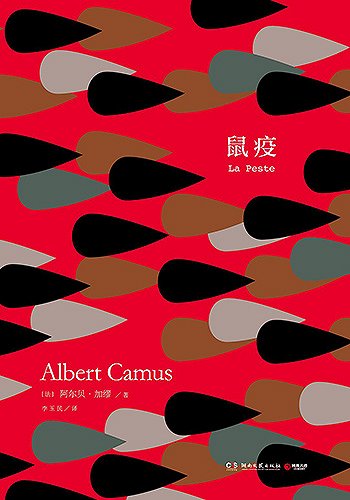
《鼠疫》 [法]阿爾貝·加繆 著李玉民 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8-3
在《鼠疫》一書中,裏厄就像奧馬爾·塔哈一樣,後者是邁蒙尼德醫院的肺病和重症監護專家,曾將自己的角色比作軍人。他明白,唯一的確定性就是工作。“其餘之事都懸在線上,在不知不覺中移動着,人們不能在此糾纏不休。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本職工作。”
讀完《恥》之後再讀《鼠疫》,令人唏噓不已。我被加繆筆下令人欽佩的主人公、庫切筆下不那麼令人同情的主人公和今天在前線的醫務工作者的經歷之間驚人重合所吸引。
《恥》中魯裏教授的醜聞發生後,他在女兒的介紹下認識了朋友貝芙。貝芙經營着一家動物收容所,由於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魯裏只好在那裏幫忙。不久,他發現自己完成了一項任務,這實際是小說的道德中心:通過注射一隻接一隻地殺死被遺棄的狗。
這些狗是人類冷漠之瘟疫的受害者,甚至反映了人類更無人格的一面。“(它們)被犬瘟熱、斷肢、感染的咬傷、疥瘡、良性或惡性的忽視、年老、營養不良、腸道寄生蟲咬傷所困擾,但最重要的是被它們自己的生育能力所困擾。實在是有太多狗了。”
把這些狗帶到診所的人,希望貝芙“處理掉(狗),讓它消失,讓它被遺忘”。庫切寫道,人們要求的是一種“昇華”,“就像酒精從水中昇華一樣,沒有殘留,沒有回味。”
但是還有殘留的屍體,這纔是真正的恥辱。魯裏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件事。他把屍體裝在袋子裏,送到醫院後面的爐子裏焚燒。換句話說,他“照顧”它們。
人類不是狗。但我們每個人在死後都會留下這樣的殘留物,一具必須處理掉的屍體,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這一事實的恥辱可能要到死亡來臨時纔會打擊到我們。但它會影響我們所愛的人和那些沒能拯救我們的人。魯裏認爲,當他按住它們不動時,這些註定要死的狗可以聞到他的恥辱和羞恥,“針找到了靜脈,藥物擊中了心臟,腿扣住了,眼睛模糊了。”他無法習慣自己的工作。開車回家時,這個精神萎靡、道德敗壞的男人不得不停車來恢復元氣。“淚水止不住地從他臉上流下來,他的手在顫抖。”
但工作還在繼續。魯裏因爲他不太明白的原因繼續做着他的工作。他只知道,“一旦它們完完全全不能照顧自己的時候,他準備好照顧它們了。”
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所以讓我澄清一下:我不是把死於Covid-19的人類比作狗,也不是把竭盡全力挽救生命的醫院工作人員比作給動物注射致命藥物的人。我想說的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我們人類共同的無助——《鼠疫》和《恥》都是關於人類的無助。
在庫切冷酷的筆法下,《恥》實際是一本極富同情心的書。它講述的是我們如何努力去照顧彼此,雖然有時暫時可以成功,但最終總會失敗。我們可能會努力避免傷害到我們所愛的人,甚至是那些被忽視、被遺棄或不被愛的陌生人。但我們無能爲力,即使是在普通的情況下,我們也無力阻止最終會發生在他們、你和我身上的一件事:經歷從生到死的屈辱。
每一次死亡都會讓我們明白這一點。但是,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情況卻讓這一點變得相當殘酷。病人們正在死亡,恐懼和孤獨地死去,人數衆多。像麥蒙尼德醫療中心賈內特·佩雷斯這樣的護士們,他們在檢查監護儀和重新插管的間隙,給垂死的病人唱歌,陪他們聊天。佩雷斯告訴《華盛頓郵報》,“我跟他們聊天,就像在跟我的家人和朋友聊天一樣。”
在《恥》的動物診所中,貝芙盡她最大的努力幫助動物們度過難關:“我不認爲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在沒有陪伴的情況下,準備好了去死。”當他們進行這項嚴峻的工作時,魯裏和貝芙不會說話。“(魯裏)現在已經從她那裏學會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們要殺的動物身上,他給這種行爲起一個他不再難以啓齒的名字:愛。”
本文作者Sebastian Smee是一位藝術評論家。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