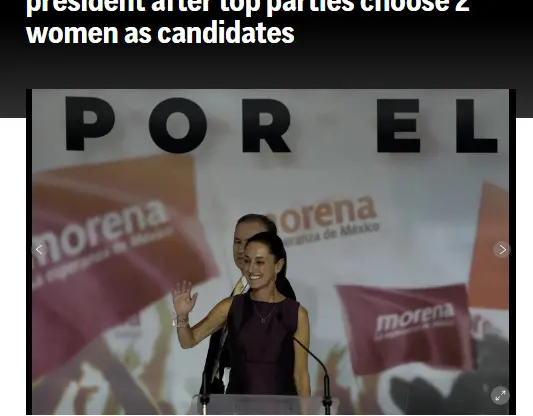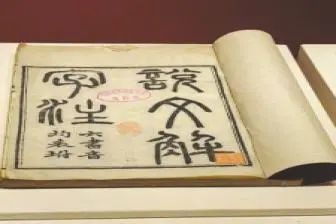越南裔美國作家阮清越的第二部小說《踐諾者》( The Committed )是他的成名作《同情者》的續篇。《同情者》是一部以越南戰爭爲背景的間諜驚悚小說,既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也是2016年普利策小說獎得主。《同情者》奠定了阮清越的文學明星地位,也讓他成爲了全世界流離失所者的代言人。在《踐諾者》中,他的無名主人公以難民身份來到20世紀70年代的巴黎,在販毒的黑幫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理論中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阮清越是南加州大學英語與美國研究、種族與比較文學的教授,也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評論員。
你曾說過,你寫作第一部小說很輕鬆。在獲得普利策獎後,寫第二部小說是什麼感覺?
阮清越: 這當然更具挑戰性,不一定是因爲期望值的提高,而是因爲我爲普利策獎做的各種宣傳。做採訪、講座,這些活動耗費了我的精力。寫《同情者》的時候,我有兩年的時間完全專注於此,因爲沒有人知道我是誰。而寫《踐諾者》的時候,我不得不斷斷續續地寫,因爲有很多幹擾。
那麼,你是如何克服這種脫節感的?
阮清越: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這本小說有大綱,我一般都會忠實地按照大綱來寫。我會50頁、50頁地寫作,在獲得普利策獎之前是這樣。接下來幾年,我的生活變得非常混亂,那時我寫了這本書的中間部分。到最後,我終於想明白怎樣平衡對我提出的各種要求,感覺自己又回到了狀態。

《踐諾者》
你的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取材於自己的生活經驗?
阮清越: 在這兩本小說中,敘述者是一個有兩種思想和兩張面孔的人,我也差不多是這樣。這就是我作爲一個難民在美國成長的感受。作爲一個越南人和美國亞裔,我總是從內外兩個角度審視自己。無論我身處何地,總覺得自己流離失所,總覺得不自在。在《同情者》中,我把這種感覺融入了小說,將其誇張地表現出來,讓這些感覺和主人公的處境更戲劇化。在《踐諾者》中我繼續了這一過程。我也曾在巴黎和法國生活過,我也思考過主人公針對法國種族主義和法國殖民主義方面所做出的思考。在這部續集中,我還想讓人們更加關注主人公對女性和性的態度:他對女性的物化傾向。這也是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的革命政治的一部分,而在這第二部小說中,他開始有所意識了。
在兩部小說中,你經常用幽默來引出創傷。你的主人公似乎曾經被流離失所的感覺所折磨,又總是同樣地被他的困境所逗樂。
阮清越: 在審視殖民主義、共產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局勢時,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拿來取笑。關鍵總是要在喜劇和點睛之筆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也要立足於歷史和政治。每一個低級笑話,比如說關於身體的笑話,都立足於這樣的問題中:這些更強大的權力是如何準確地通過我們的身體來運作的,並試圖讓我們忽略那些確實就在我們眼前的東西?我們看不到它們,因爲它們已經被正常化了,但如果我們去掉這些正常化的視角,幽默感就會顯現出來。

《同情者》 [美]阮清越 著 陳恆仕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8
《同情者》在2015年出版時,你成爲了難民危機的重要代言人。你認爲我們從那個時候以及敘利亞內戰的餘波中學到了什麼有用的東西嗎?
阮清越: 難民危機還在繼續:一方面,政治和經濟根源導致大量人口流離失所,另一方面,對人口流動的恐懼依然存在。2015年前後,大約有6000萬人流離失所。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現在這個數字大約是8000萬。從這些數據中,我看不出我們在處理這些危機方面做得更好了。
對你來說,危機的根源是什麼?
阮清越: 就叫它殖民化吧。這是如今很多問題的簡寫。難民危機、毒品戰爭、種族間的暴力。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我們所處的這段長達五百年的歷史史詩——殖民化。它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歐洲現代性的興起緊密相連,並發展到美國。而即使去殖民化已經合法地發生了,但如果從被殖民國家是否真的擺脫了外國統治這層意義上說,去殖民化實際上還沒有發生。前殖民地國家在文化和政治上仍有創傷,他們仍然有從殖民者那裏繼承來的社會等級結構和自我仇恨的心理結構。而不管是西歐國家還是美國,這些前殖民大國仍然擁有幾個世紀積累下來的所有財富和權力。種族主義和父權制的力量是殖民化運作的根本,並且仍然根植於我們的社會和內心。
《承諾》中的主人公似乎一直在糾結於典型的後殖民作家,尤其是弗朗茨·法農和艾梅·塞澤爾。這兩位中哪位對你的思想影響最大?
阮清越: 法農。我一直在回味《黑皮膚,白麪具》這本書,因爲它描述了被殖民的狀況,尤其是對男人而言。(對女性來說就不是這樣了。)它試圖解答的是種族與普遍性之間的問題,而法農在書中說的一切放在現在也是絕對貼切的。既想做普通人、又完全清楚不能擺脫種族主義賦予你的皮膚,他很精準地描述了這種兩難的境地。
拜登已經在轟炸敘利亞了。說到美國帝國主義,你相信拜登在任何方面都會是一個比特朗普更好的總統嗎?
阮清越: 不,我不這麼認爲。我敢肯定,華盛頓的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共和黨人,都鬆了一口氣,因爲拜登帶來的是美國帝國主義作爲外交政策的更高效的迴歸。我鬆了一口氣,是因爲我不用再惦記着特朗普和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政策,以及我認爲他的對億萬富翁友好的經濟政策。但在我看來,毫無疑問,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下,美國仍將延續一貫的方式。拜登幾乎立即將轟炸作爲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這既是可以預見的,同時也是非常可悲的。
你此刻在讀什麼書?
阮清越: 我不能告訴你,因爲我是今年普利策委員會的一員,我正在閱讀所有的普利策提名作品,它們都寫得很棒——但提名的書籍也是保密的。
好吧,那30年前,在你20歲出頭的時候,讀的是誰的書?
阮清越: 託尼・莫里森、詹姆斯·鮑德溫、拉爾夫·埃裏森,還有美國黑人作家。作爲一個亞裔美國人,真正的衝擊是長大後發現還有亞裔美國作家。我什麼都不知道,直到上了大學才發現其實亞裔美國人已經寫了近一個世紀了。包括第一位華裔美國作家蘇新發;卡洛斯·卜婁杉,第一批主要的菲律賓裔美國作家之一;約翰·岡田,第一個寫被關押的日裔美國人的作家。
如果你被困在荒島上,只能讀一本書,會是哪一本?
阮清越: 《堂吉訶德》。
現在你出名了,你的學生會不會更關注你?
阮清越: 我不知道。我的解答時間(學生可以預訂一個時段,與教授談論他們的學習進度)並沒有學生光顧。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