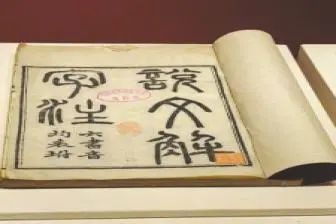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早逝之前兩年反思自己的事業時,將自己描述爲一個“爲他人指明道路的路標,而自己卻被迫在泥濘和塵埃中站立不動”的人。事實上她很少站在原地不動,但現在看來,這句自我描述顯得尤其貼切——在倫敦北部紐靈頓綠地,一尊紀念她的裸體女性雕像日前揭幕,卻被抹上了許多批評的泥巴。在去世幾個世紀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仍然在引發爭議。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位勤奮的文學專業人士,1780年代末被捲入歷史的浪潮之中,此後與歷史共浮沉,這既爲她贏得了名聲,也引來了惡名。她是一個來自不健全家庭的不幸女孩,成長爲了一個充滿怨氣、情感需要和知識慾望的女人。她是一個嚴厲的批評者,尤其是對自己。隨着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她把批判的火力轉向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從對1790年埃德蒙·伯克攻擊法國大革命的激烈反駁,到對各派”專制“思想家尤其是男性特權的維護者進行大刀闊斧的攻擊。她是一個酗酒家暴者的女兒,揭露男性對女性的“專橫野蠻”統治,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著名作品《女權辯護》的目標。她在之後的著作中一再回到這個主題,直到1797年38歲的她在分娩時去世。
她短暫的一生以大膽和不循規蹈矩爲特點。她曾告訴一位童年好友,自己寧願“與任何障礙做鬥爭,而不是進入一種依賴狀態”。成年後,她在資源極少的情況下,決心在英國這個階級森嚴的父權社會中儘可能自由地生活。她孜孜不倦地努力自我教育,只在學校接受了最基本的閱讀和寫作教育,卻精通四種語言,熟知啓蒙思想的所有主要內容。
從19歲起,她就自食其力,生活常常陷入拮据。但當她第一個女兒的花心父親爲了一位演員拋棄她,並提出向她提供經濟資助時,她拒絕了。“我不想要這種庸俗的安慰,也不會接受,”她告訴吉爾伯特・伊姆萊。她的下一個情人,激進哲學家威廉·戈德溫,同樣被告知她決心用筆“賺取我想要的錢”,否則就“永遠睡去”。她懷着在未來寫出《弗蘭肯斯坦》的女兒瑪麗·雪萊嫁給了戈德溫,卻堅持分居,並深情寫道:“我從靈魂上希望你駐紮在我心中,但我不希望你總是在我的肘旁。”
然而,這種驕傲的獨立,被情感上深深的不安全感,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描述的由她年輕時的“艱苦奮鬥”所誘發的“憂鬱的人生觀”所抵消。她很少了解或期望簡單的感情,她告訴了伊姆萊,因爲他也表現出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對愛情的渴望是激烈的,而失去愛情又是無法忍受的。伊姆萊的拋棄讓她兩次試圖自殺,哪怕她的生活和思想都以宗教信仰爲基礎。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後不久,戈德溫出版了一本關於妻子的回憶錄,對她的名聲造成了長達幾十年的詆譭。直到20世紀,特別是隨着女性解放運動的興起,她纔有了今天的英雄地位。
“當我們被迫去感受時,我們纔會深刻地辨析。”179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這樣評價自己。西爾瓦娜·托馬塞利(Sylvana Tomaselli)的新作《沃斯通克拉夫特:哲學、激情和政治》( Wollstonecraft: Philosophy, Passion and Politics )在她的感情和思辨之間遊走,繪製出了一幅新鮮而引人注目的肖像。從“她喜歡和熱愛的東西”開始(所有章節的標題都讓人聯想到那個時期的小說),這本書以獨闢蹊徑的方式分析了她的作品 。我們瞭解到她對戲劇和音樂的熱愛,她的閱讀品味,尤其是她對詩歌的熱愛,以及她對自然之美的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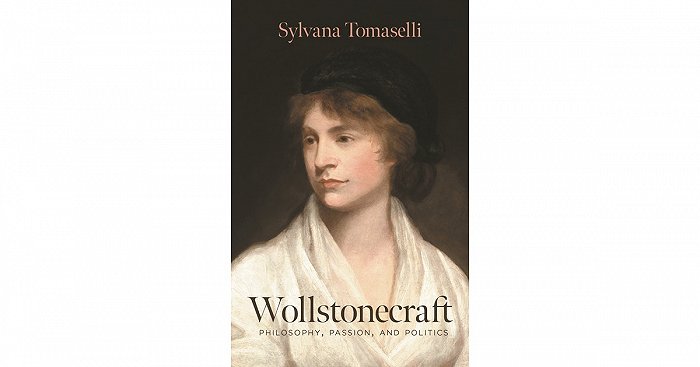
《沃斯通克拉夫特》
沃斯通克拉夫特總是被描繪成一個掃興的人(女權主義者經常被如此形容),但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她擁抱生活的樂趣。她是一個有着無拘無束的生命力的女人,我最喜歡的一個畫面——雖然沒有出現在這本書中——是她獨自在瑞典一個山坡上,她攀爬在高高的岩石上,享受着每一分鐘。我們還能看到她作爲朋友和情人的樣子,見證她濃烈的感情,只不過她的快樂往往被痛苦所取代。但是,如果說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個有着強烈的愛的女人,那麼她也如戈德溫所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憎惡者”——西爾瓦娜·托馬塞利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講述她對社會的憎惡,以及她如何旨在改變這個社會。
《女權辯護》讓沃斯通克拉夫特成爲名人,她是“女性權利的維護者”,是將女權主義推上政治舞臺的“亞馬遜女哲學家”,但這不是她在本書中的形象。托馬塞利一方面承認沃斯通克拉夫特憤怒於社會對待自己性別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想用她的啓蒙知識分子形象來取代她女權主義先驅的形象,因爲她對女性的看法只是廣泛的“人性哲學”的一部分。《女權辯護》作爲沃斯通克拉夫特決定性作品的地位應該被“取消”,代之以《人權辯護》(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這是她早先對伯克的回信,展現了某種在托馬塞利看來她思想的基本特徵:她對現代“文明”(civilisation,18世紀的一種說法)的嚴厲批判,以及她對建立在人類道德改革基礎上的自由、平等和社會正義的“真正文明”的革命方案。
這種對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寬泛視角,並不是托馬塞利所暗示的與現有學術的徹底決裂。最近大多數研究也是如此,儘管許多人將她的政治思想與某種“主義”接軌:自由主義、公民人文主義、共和主義。托馬塞利拒絕了這類標籤,認爲它們具有誤導性和/或不合時宜。相反,她巧妙地將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出名的作品(如她的書評)中的材料與她主要的非虛構文本交織在一起,以捕捉其哲學的“基調和精神”,同時突出其強烈的歷史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從《人權辯護》開始就很明顯。當“一種新的精神出現,來組織身體-政治”時,文明世界是如何走到當前的關鍵時刻的?這一變革時刻又會帶來什麼?正如托馬塞利所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所有思想都被這些問題,以及對人類潛能和神聖意圖的綜合信仰所框定——即使是在法國恐怖事件之後,她仍然堅信一個“更平等的自由、人類普遍幸福”的時代最終會到來。
一個勇敢的女人抱有勇敢的希望。我們更應該紀念這位勇敢的啓蒙哲學家沃斯通克拉夫特,而不是作爲女權主義者開路先鋒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嗎?不,“女權主義者”固然不合時宜(這個詞直到19世紀末纔開始使用),但從1792年開始,“對我的性別的壓迫”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關心的問題,她不斷地書寫這個主題,並對其進行深刻的辨析。她關於這個主題的著作會讓人感到驚愕,尤其是《女權辯護》。這部作品對女性的缺點進行了激烈的譴責:她們的非理性、嬌氣、輕浮,以及——也許最讓現代讀者不齒的——女性的感性,她們心甘情願地被“隨意的情慾”所奴役。這種審查性是她那個時代前女權主義寫作的典型特點,並且處於變化之中。但托馬塞利沒有注意到這些變化:她着手頌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哲學家的面向,卻沒有追蹤她的思想成長,從而削弱了她作爲思想家的身份。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中充滿了不一致和悖論。托馬塞利承認這一點卻並不重視,而是儘可能地尋求調和立場的互斥。但人們往往是通過這些張力來理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這既凸顯了她正在與之鬥爭的問題的新穎性和複雜性,也凸顯了她爲這些問題注入的創造性,隨着瞭解更多和思考更多,她就會轉變策略。她不是一個學者,而是一個革命者:單純的一致性對她來說有何意義?
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時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說《瑪麗亞或,女性的錯誤》( 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 ),於她去世後的1798年出版。在這本非同尋常的書中,她公開爲女性非法的性快感辯護(一個多世紀以來,女權主義內部沒有再次提到過這個話題)。也許更重要的是,她還通過探索階級和性別壓迫之間的聯繫,首次嘗試解釋交叉性理論。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中的這些重大發展,並沒有出現在托馬塞利的書中,因爲作爲一個政治哲學家而非文學學者,作者避開了所有對於小說的討論。
但是,我們不能把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哲學家身份與發揮想象力寫作的作家身份分開,正如她在第一部小說《瑪麗:一部小說》( Mary, A Fiction )導言中所寫的那樣,寫作帶來的是“可能性”——無論是關於她的性別還是關於整個人類。托馬塞利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精美的肖像畫,其中蘊含着豐富的見解,但要想充分領略這位被廣泛(也是有爭議的)頌揚勇敢、熱愛自由的女性(順便說一句,她本人並不喜歡勇敢的熱愛自由的女性被描繪成一個女英雄),我們需要一幅更完整、更有活力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畫像,她對自己性別的平等主義雄心壯志在今天還遠未實現。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