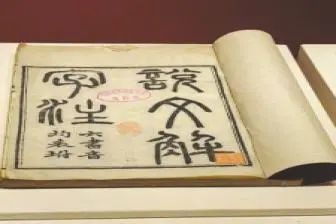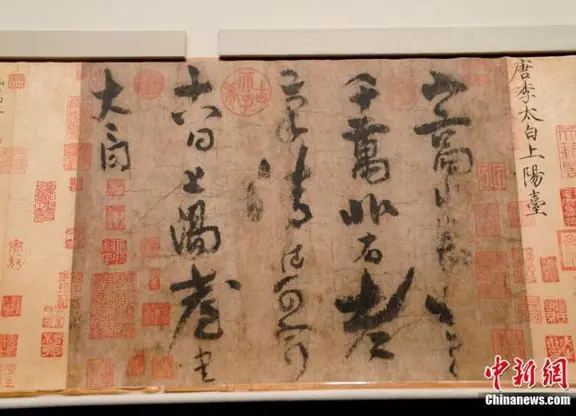身爲波蘭作家,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卻在“波蘭性”之外擁有“非波蘭性”。怪誕新奇的想法、溫柔細緻的筆觸、碎片化的敘事結構、對當代社會的深刻關懷,都使得託卡爾丘克在波蘭文學、世界文學的版圖中別具一格。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發言詞中,託卡爾丘克稱呼自己爲一個“溫柔的講述者”,她用跳躍式的碎片寫作,呼喚着對人類世界的大愛。
日前,託卡爾丘克的最新小說集《怪誕故事集》中文版被引進。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它是反日常的奇異行文。新書出版之際,單向街書店舉辦了名爲“在託卡爾丘克的‘怪誕’文學罐頭裏想象未來”的在線講座,作家李洱,《世界文學》雜誌主編高興,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學院院長趙剛,《怪誕故事集》譯者李怡楠等嘉賓參與分享。幾位嘉賓都指出,託卡爾丘克值得每個讀者細讀,因爲她的文學空間足夠廣博,能夠容納每一個擁有不同經驗的讀者,以獨特的方式找尋到真實世界中發生的“怪誕”。

《怪誕故事集》 [波蘭]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著 李怡楠 譯 可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0-7
託卡爾丘克與波蘭文學
波蘭是中東歐文學的重鎮。在託卡爾丘克獲獎之前,亨利克·顯克維奇(1905年)、弗拉迪斯拉夫·萊蒙特(1924年)、切·米沃什(1980年)、維斯瓦娃·辛波絲卡(1996年)這五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已經令波蘭文學享有盛譽。爲什麼波蘭能夠產生如此重量級的文學?趙剛指出,波蘭是一個處於“擠壓”中的民族國家。在地緣政治的角度中,“擠壓”通常被用來形容東西方角力下的現實處境。但現代波蘭文學擁有更多角度——東西方文化、不同宗教、傳統和現代、野蠻和文明不同的價值觀都會導致“擠壓”。這片土地生產出的“擠壓”恰好使文學達到了一個高度。華沙大學心理學出身的託卡爾丘克,以舒緩溫柔的語調講述這種“擠壓”的狀態,是非常獨特的存在。
波蘭文學史大致分兩種流派:以顯克維奇、萊蒙特、米沃什爲代表的一派,作品中充滿愛國、奮鬥、自強的民族精神,象徵着本土“波蘭性”;另一派以維托爾德·貢布洛維奇、布魯諾·舒爾茨爲主,持冷靜客觀的態度,爲波蘭沉重的民族性加入了輕盈的東西。
高興認爲,託卡爾丘克既具有“波蘭性”,又具有“非波蘭性”。她有着描繪龐大歷史的能力,但也能述說怪誕的想象,熟練運用舒爾茨般的變形和暗喻。“在各個文體領域間順暢騰躍”,正是託卡爾丘克的獨特之處。託卡爾丘克不拒絕講故事,強調講故事的重要性。比起解構者這個身份,她更像一個建構者,圍繞着一定的意義構建小說。高興指出,託卡爾丘克的文學世界有一種溫柔的、輕盈的魅力,吸引着讀者進入。除了豐富性、碎片化、雜糅式的寫作外,託卡爾丘克多樣的風格和手法也讓人吃驚。她認爲世界處於瞬息萬變中,需要用無窮的語調來抓住這個世界。
“強烈的中和性”是李洱對《怪誕故事集》的評價。這也是最近20年世界小說發展的潮流。文體在傳統講故事之外,還有着遊記、日記、神話、童話等特徵。託卡爾丘克本人的思維特徵則受榮格影響,認爲神話故事從未發生,但神話思維一直存在。這導致她的作品往往溢出日常經驗,帶有神話或通話特質。同樣的“中和性”還體現在對人和自然、社會主義、後社會主義等關係上。
李洱用託卡爾丘克在《罐頭》一篇中寫到的“魔菇”舉例,認爲託卡爾丘克在描寫蘑菇時異常細緻,是她親近自然的體現。李洱認爲蘑菇是既非動物或植物的蕨類,而《怪誕故事集》也可以看成是“蘑菇”般的存在:它產生於神話思維和日常思維之間,文體則介於人物傳記和童話故事之中。“這是‘作爲一種方法’的託卡爾丘克。”
另外,這種碎片化的寫作是託卡爾丘克迴應時代的一種方式。互聯網時代消解了傳統的敘事方式,令人們必須處理大衆傳媒帶來的衝擊和擠壓。作家作爲故事的講述人,尤其需要調整姿態。託卡爾丘克的應對是將故事碎裂成一個個短小篇章,它們都處於某種“擠壓”之中。她用非虛構手段處理虛構性故事,這對時代構成了雙重呼應:既面對了現實,又對提供了“惡的信息”的時代進行了強烈質疑。
關於“碎片化的問題”,李怡楠稱這是託卡爾丘克特有的手法:用長短篇的切換,來回應一個碎片化的時代。託卡爾丘克本身崇尚短篇,她在波蘭舉辦短故事節,認爲長篇讓人進入到恍惚的狀態,但短篇卻對作家能力要求更高。身爲譯者,李怡楠特別指出託卡爾丘克特有的“溫情”“溫柔”“敏感”“共情”等氣質貫穿了她所有的創作。
《怪誕故事集》與託卡爾丘克的文學世界
“怪誕”是託卡爾丘克自創的詞語,原文是法語,指的是荒誕、奇幻等各種元素的集合。它不是“奇幻”“魔幻”,更像是與社會大背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經驗,令人體味到一種急需控制的異物感。李怡楠說她翻譯《旅客》時“冒冷汗”。《旅客》中的主人公身處長途旅行的飛機,身旁的陌生人向他講起童年時的恐怖經歷,這個似夢非夢的過程近似驚悚片,有着巨大的衝擊感。儘管託卡爾丘克描述的盡是荒誕與不可思議的事物,但它們都來自今天的日常生活。其實,以“怪誕”爲名的故事集沒有想象中的驚悚,它以溫柔的方式邀請每個讀者來仔細閱讀,讀者們也能通過各自的方式來找到他們自己的故事。
《怪誕故事集》收錄了10個故事。這些故事的多樣性不僅體現在題材上,還在於大量豐富的細節,因爲它們能夠指向多重解釋方式。《罐頭》中描寫母親去世後留下的奇奇怪怪的罐頭。《接縫》描寫一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了難以接受的變化,陷入自我懷疑。《拜訪》《變形中心》《心臟》等帶有科幻色彩,《萬聖山》《人類的節日年曆》則有宗教元素。
託卡爾丘克涉獵頗廣,人類學、心理學、植物學和醫學都有所涉及。她生產出的文學卻碎片化,糅合着巨大的合成感。這種精心安排的碎片作品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間,但需要讀者主動進入,用自己的閱讀經驗尋找“怪誕”故事的答案。答案不是現成的,有時甚至沒有“答案”。世界的“有解”和“無解”,都是託卡爾丘克想表達的。
《罐頭》中的主人公是“啃老族”,當母親去世之後,懶漢面臨無所依靠的處境,他只能依靠母親留下的罐頭維生,但故事的轉折點正是這些罐頭。《拜訪》不是典型的科幻小說,探討人工智能將把人類世界引向何方。它所顯示的是程序化的生活,井井有條的一切正好被兩個人的突然拜訪打破。託卡爾丘克以心理的、隱喻的和文學的手法藏匿了批判的鋒芒,提出了關於世界結構與未來發展的可能猜想,“這樣一個世界,彷彿我們的時間在沿着一個蝸牛的殼向前爬行,越往殼裏面走,它的結構越精密,但是空間也越狹窄。”
趙剛稱,託卡爾丘克爲整個當代文學“闖新路”。他認爲現代文學的創作方式進入了難以突破的階段,但託卡爾丘克卻能在短短几頁內間開創出一個新的空間。《綠孩子》提到波蘭在17世紀時遭遇的戰爭。點到爲止,不會讓不熟悉波蘭歷史的讀者覺得難讀,也留下開放性令人思考。除了歷史外,《綠孩子》還涉及文明中心論、人與自然等主題。故事的起因是一位法國醫生前來波蘭,爲國王療傷。途徑森林時醫生髮現了兩個受傷男孩,他進行了醫療,孩子卻遭到了死亡。在這個故事中,託卡爾丘克對人與自然的同一性做出探討。孩子們除了皮膚是綠色的,“不需要吃太多東西”“既不種地,也不蓋房子”之外,和人們沒什麼區別。在託卡爾丘克的世界中,人與自然沒有邊界,兩者之間不存在絕對對立,它們始終融合,具有很強的同一性。
李洱則提到託卡爾丘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講。在演講中,作家提出第一人稱敘事“完全改寫了世界的敘事”,令文學受衆基於同理心彼此理解。但大衆傳媒盛行的當代給予所有人發聲權利,獨特的“自我”隨之湮滅在“衆聲喧譁”的世界。這時,從“第一人稱”轉變到“第三人稱”是一個必須的抉擇。
另外,這本《怪誕故事集》在託卡爾丘克的創作序列中是“速寫”的存在。作者匆忙講述,記錄碎片,這些故事的形態不完整,類似卡夫卡的筆記。同爲小說家的李洱猜想這可能是一部長篇小說成型前的準備階段。託卡爾丘克也經常強調“經驗”這個詞,它不是生活的復刻,而是對生活的記憶和反省。它是生活、記憶和時代的某個肖像,用速寫形式記錄文學上的篇章,預示着作家會用這些片段寫出更完整的文字。
在當今世界,文學的作用是什麼?
在諾獎演講中,託卡爾丘克描述如今的世界是“貪婪、不尊重自然、自私、缺乏想象力、無休止的競爭和喪失責任感,這些已使世界淪落爲一個物體,可以被切成碎片,被耗盡,被毀滅。”她在創作過程中也傳遞了人文主義的關懷。李洱認爲,用文學回應一個不斷潰敗的世界,“這是當代有責任的作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他引用託卡爾丘克“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因爲在一個越來越怪誕的時代,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高興則指出寫作的內在動力成爲箇中關鍵,託卡爾丘克是一位真誠溫柔的寫作者,她認識並相信寫作的意義。託卡爾丘克在諾獎演講詞開頭提到一張母親的照片,她認爲她從中看到了“靈魂”的重要性。而正是“靈魂”,令她成爲一個溫柔的講述者。託卡爾丘克不相信文學能夠大衆化,它是少數人能夠理解的事物。但她相信,正是一些有靈魂意識與良知的作家,用心靈傳達世界的經驗,令文學不再是職業,而是事業。文學的細節和經驗源自心靈、頭腦和靈魂意識,託卡爾丘克的的作品給人生和世界提供了可能,她的細節令人反覆感動。趙剛也認爲,託卡爾丘克從細微之處入手述說世界的手法,在這個秩序碎片化的世界中有着精神價值:她爲萬物發聲,也爲不發聲的事物發聲。
託卡爾丘克的短篇小說集《衣櫃》即將出版中文版,其中《房號》一篇的靈感可能來源於託卡爾丘克的個人經驗——她曾做服務員來補貼寫作。《房號》以碎片式的場景描繪芸芸衆生,只有進入每個房間的服務員才能與衆人產生隱祕的聯繫。李怡楠認爲,這就像是託卡爾丘克看待文學的方式。她用文學聯結起自己、讀者與世界,在基於共情的理解中實現教育與啓迪。
李怡楠推薦青年人來閱讀託卡爾丘克。文學能夠帶來啓迪,激發細微的衝動,令人瞭解日常外的世界。青年人能夠通過文學關注他人的生活,在代入的過程中思考。正如託卡爾丘克所說的那樣,“文學是爲數不多的使我們關注世界具體情形的領域之一,因爲從本質上講,它始終是’心理的’。它重視人物的內在關係和動機,揭示其他人以任何其他方式都無法獲得的經歷,激發讀者對其行爲的心理學解讀。只有文學才能使我們深入探知另一個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觀點,分享他的感受,體驗他的命運。”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