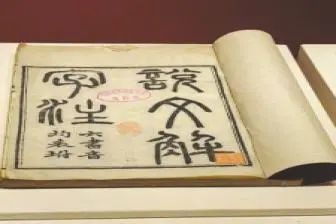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金鳳花的祕密——植物性別政治的無知學解釋》
文 | 姜虹(《讀書》2021年3期新刊)
“沒有得到荷蘭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爲了不讓子女像自己一樣淪爲奴隸,他們用[這種植物]的種子墮胎。”十七世紀探險博物學家瑪麗亞·梅里安在《蘇里南昆蟲變態圖譜》中提到的種子來自豆科的金鳳花(Caesalpiniapulcherrima),原產美洲熱帶和亞熱帶,在世界各地廣有栽培,包括我國南方。然而,金鳳花在全球傳播、引種栽培的過程中,關於這種植物的隱祕知識——梅里安提到的墮胎藥性,卻沒有跟隨植物本身傳播。火焰般絢爛的金鳳花深受人們喜愛,但它作爲墮胎藥的知識鮮爲人知,歐洲博物學家在三百多年前就知道的知識爲何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了斷裂?“我們知道什麼?爲什麼知道?”——這是知識生產與傳播研究的常見問題,但鮮有人試圖回答:“我們不知道什麼?爲什麼不知道?”這就是隆達·施賓格在《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中以金鳳花爲案例所要回答的問題,她採用了科學史家羅伯特·普羅克特稱之爲“無知學”(agnotology)的方法論。

瑪麗亞·梅里安《蘇里南昆蟲變態圖譜》中的金鳳花插圖
《植物與帝國》探討了名不見經傳的植物——金鳳花,它並沒有像金雞納、罌粟、茶葉、土豆等植物那樣對世界的政治、經濟產生過巨大影響,即使作爲觀賞植物也未曾像玫瑰或鬱金香般被狂熱追捧。金鳳花的特殊性在於其重要的政治意義,“在整個十八世紀,金鳳花被奴隸婦女當作反抗奴隸制的武器,她們用這種植物讓自己流產,以免孩子生而爲奴”(5頁)。其特殊性還在於,它作爲墮胎藥的知識並沒有因爲廣泛引種被傳播到歐洲。金鳳花因此成爲植物性別政治研究的絕佳案例,反映了歐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性別關係對歐洲博物學家生物勘探和移植的影響,也成爲無知學的典型案例。“無知往往不僅是知識的欠缺,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結果,畢竟大自然有着無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我們對某個時期或地方知道什麼或不知道什麼,都會受到特定的歷史條件、本土和全球的關注重點、資金分配模式、機構和學科等級、個人和專業的眼界以及其他衆多因素的影響。”(2—3頁)施賓格在無知學的解釋框架下,探討了植物的性別政治,並以此闡釋知識體系的構建和文化因素導致的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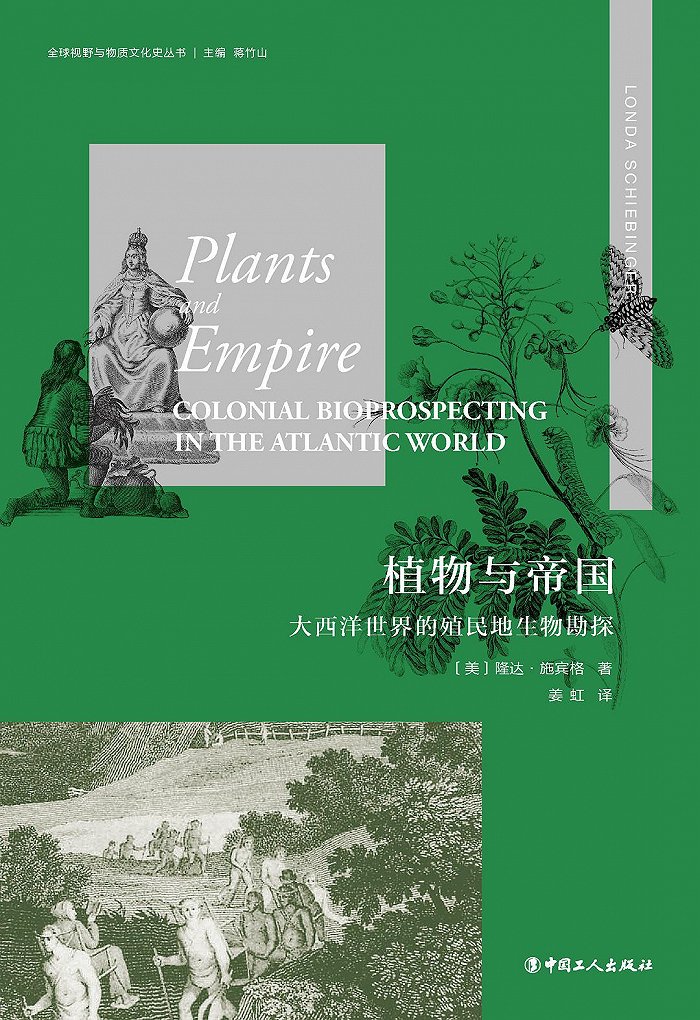
《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美]隆達·施賓格 著 姜虹 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20-11
生物接觸地帶的知識、女性身體與政治
施賓格將瑪麗·普拉特《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裏的“接觸地帶”具體化爲“生物接觸地帶”(biocontactzones),聚焦於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在加勒比殖民地的相遇,“以探討歐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這幾類博物學家的互動,並突出該語境下植物以及它們在各種文化中的用途信息的交換和傳播”(101頁)。生物接觸地帶的藥物勘探是歐洲博物學家的主要目標,奴隸和本土人積累的大量醫藥知識成爲博物學家攫取的對象。然而,如何有效獲取這些知識?跨文化的知識交流面臨着各種障礙。在語言上,在接觸地帶形成的混雜文化和語言對交流有所幫助,但歐洲人不懂(或者不願意學)本地語言和本地人對宗主國的抗拒等原因阻礙了交流,歐洲人常常只能瞭解一點皮毛知識。殖民關係中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促使奴隸和印第安人嚴守自己的醫藥知識,拒絕提供給征服者,歐洲人不得不採用“收買、乞求和盜取”等非正當手段獲取這些祕密。而生物接觸地帶的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因爲種族、階層和性別等因素被多重邊緣化,她們所掌握的醫藥和植物知識顯得更加隱祕,也極少以文字留存。尤其是關於她們自身的疾病、治療和生育等知識,通常僅限於女性之間傳播,從她們身上獲取本土知識自然更加困難。例如,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醫生愛德華·艾維斯在印度想收買一位葡萄牙寡婦的治性病祕方,被拒絕後他竟然派人跟蹤對方,最終找到了有神奇療效的植物(90—91頁)。不同的經濟利益和文化目標也加劇了交流的障礙,對印第安人來說樹木能否造船、果實是否可食遠比歐洲博物學家關心的分類特徵重要。歐洲人對自己的知識體系充滿自信和優越感,不屑於原始、落後的本土知識,他們將植物活體或標本剝離原本的自然和文化環境,引種到歐洲的植物園和私家花園,或者陳列於珍奇櫃,用“統一”的分類體系和命名法則進行歸類和命名。在施賓格看來,“標準”以拉丁文爲全世界植物定名的做法,無異於一種“語言帝國主義”,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認識論立場,扼殺了知識和文化的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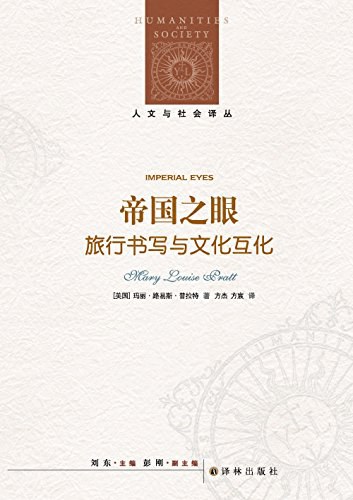
《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
具體到女性身體、疾病和生育的知識,尤其是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的墮胎實踐和藥物知識,情況則更加複雜微妙。在殖民擴張的背景中,女性的身體被物化成歐洲的財產和征服工具。歐洲底層女性曾被運送到殖民地,以平衡歐洲殖民者嚴重失調的男女比例。奴隸女性在殖民經濟和政治中則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她們的身體淪爲性工具和生育工具。“歐洲男性想當然地認爲可以恣意佔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結構極爲年輕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約,以及最重要的一點,殖民地的主要人口……都是暴躁的男性。”(158頁)她們不得不爲奴隸主和其他歐洲人提供性服務,即使她們可能有丈夫或情人。生育則是更重要的職責,因爲在殖民地經濟中,奴隸人口的健康和增長與經濟繁榮緊密相連。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奴隸貿易遭到越來越嚴厲的批判,殖民者更加重視奴隸的生育。然而,奴隸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長率一直很低,“疾病、繁重的勞動、糟糕的生活條件和長時間哺乳對排卵功能的抑制”等原因都容易導致不孕,而墮胎也是其中一個原因(170—171頁)。

穿着晨禮服的風流種植園主人(來源:約翰·斯特德曼《鎮壓蘇里南反叛黑奴五年遠征記》,由詩人威廉·布萊克繪製)
對女性來說,墮胎(甚至弒嬰)與逃亡、自殺、怠工、造反一樣,都是殖民地奴隸反征服的政治鬥爭方式,與生育計劃關係不大。梅里安早就意識到這一點,而當時大部分歐洲醫生卻認爲,奴隸女性墮胎不過是非洲人放蕩的本性使然,因爲懷孕會減少她們的歡愉時光和賣淫收入。殖民地的歐洲醫生時時提防婦女裝病騙他們開藥,尤其是瀉藥和通經劑,以防她們用來流產,因爲醫生們認爲不少通經劑和墮胎藥並無本質區別,只是劑量上的差異。例如,漢斯·斯隆在牙買加提到一種野鳳梨時說道:“通經效果也很好,如果劑量不當,會引起大出血。它會引起孕婦流產,娼妓經常會故意用它打掉自己的孩子。”(166頁)在梅里安的探險過了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奴隸制批判者開始重申她的觀點:奴隸女性以拒絕生育報復奴隸主,讓後代免遭奴役。奴隸制的殘暴導致婦女喪失了連動物都有的母性本能,違背天性,毫無生育的慾望,甚至與接生婆密謀殺嬰。與歐洲帝國的白人女性相比,奴隸女性的身體被物化成工具和財物,也成爲她們參與政治抗爭的武器。相比性別政治,殖民統治和奴隸制對她們的壓迫更爲殘酷。
金鳳花的性別政治與無知學
金鳳花的墮胎藥性使它與加勒比地區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的生育聯繫在一起,在殖民擴張的背景中承載了重要的政治意義,成爲本書主角。作者採用國內學界還相對陌生的方法論工具——無知學,重構了金鳳花所彰顯的性別政治。無知學研究“無知”的產生以及被遺忘和遺失的知識,關注原本可以知道或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知識。既然該發生的事情沒發生,該傳播的知識沒有傳播,必然缺乏歷史記載,那該如何證明沒發生的事件和未傳播的知識?施賓格採用了比較的方法。就金鳳花而言,同時期有大量新大陸的植物得到開發利用,經過藥物實驗後被收錄在歐洲各大藥典。金鳳花能導致流產的知識沒有傳播到歐洲,不是因爲知識欠缺,而是源自政治和文化的張力。這段歷史“揭示了探險者如何在浩瀚的自然知識中進行精心挑選,他們受到國家和全球的戰略、資助和外貿模式、發展中的學科層級、個人興趣、專業需求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遺失了大量有用知識”(280頁)。
種族、性別和階級差異讓歐洲醫生難以參與奴隸女性的生育實踐和疾病醫治。她們通常在自己的小屋或種植園的“暖房”分娩,負責接生的也是奴隸女性,醫生只有在難產時纔出現。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在男醫生面前對自己的疾病也難於啓齒,社會文化環境鼓勵她們自行應對各種病症,避孕和墮胎更是女性的專屬話題。然而,與行會、商業和軍事機密不同,墮胎藥的知識並沒有因爲保密性而被隔離,也沒有像巫術那樣被列爲危險知識遭到公開禁止,至少在墮胎法案確立前如此。長期生活在殖民地的歐洲醫生和博物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殖民統治,前者維持殖民地人口(尤其是奴隸)的健康,監管奴隸的生育,後者探索本土食用植物,以降低奴隸食物的成本。他們或多或少都會了解到本土的墮胎手段和藥物,他們也非常關注這類知識,儘管很少詳細記錄。例如,著名博物學家洪堡曾震驚地發現,印第安婦女用草藥墮胎後沒有危及性命,還可以再懷孕,並以此方式計劃懷孕時間。其他歐洲人也發現黑人女性可以熟練使用草藥終止妊娠,而且效果顯著(154—155頁)。米歇爾-艾蒂安·德庫爾蒂《安的列斯羣島植物與醫藥圖鑑》最後一卷討論了十九種通經劑,其中五種在加大劑量時可以引起流產(167—168頁)。具體到金鳳花,其藥用價值在十七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一直有記載,尤其是作爲退燒藥,“在歐洲受到歡迎,對四日熱特別有效,法國軍隊醫院就因爲這個藥性進口了一些”(210頁)。它的墮胎藥性在梅里安、斯隆和德庫爾蒂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到,斯隆將其稱爲“花籬”,“能刺激經血,會引起流產”;德庫爾蒂的說法是大劑量的花(而不是梅里安說的種子)可以通經,但使用時要非常小心,因爲黑人婦女會用來墮胎(130頁,132頁)。因此,不管是金鳳花還是其他用來流產的植物,都不是因爲知識欠缺導致了歐洲人對它們的無知,而是這些知識的傳播過程被人爲終止了。
如前文所言,重商主義的歐洲帝國將人口視爲國家財富,奴隸人口被降格爲財物,即使歐洲女性也有道德上的義務,通過生育實現自己的公共價值和愛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重商主義也是強烈的多生育主義”(275頁),墮胎因此被當成罪行,墮胎藥物也被污名化。十八世紀的歐洲已有標準化的藥物實驗程序,動物實驗、人體實驗、自體實驗、性差異實驗和種族間實驗一應俱全。墮胎藥物卻沒有經過全套的實驗,甚至沒有和通經劑一樣被納入藥物實驗,儘管兩者在藥理上被認爲並無本質差別,更何況通經劑還經常被濫用。博物學家和醫生通過藥物勘探和殖民地人口管理參與帝國的戰略計劃,心照不宣地踐行着重商主義的帝國理念。他們認爲墮胎和墮胎藥不僅危險,還令人反感,他們關心的是如何預防小產以保持人口增長,無視女性對安全墮胎方法的渴望。醫生即使做了墮胎手術,也拒絕傳播相關的技術和知識。政府當局自然也不支持墮胎,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歐洲各國先後立法,將墮胎行爲定罪,墮胎藥物隨之成爲違禁藥。十八世紀牙買加衛生官員威廉·賴特在自己的藥物書裏記載了金鳳花的多種用途,卻沒有將它寫進官方報告或藥典。斯隆熱衷於推廣殖民地藥物和植物產品,他沒有大量採集金鳳花這類植物,也沒有在行醫中使用墮胎藥(211頁)。

金鳳花,楊雲拍攝於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在重商主義的殖民擴張背景中,金鳳花和其他新大陸墮胎藥物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色彩,將女性身體、性別政治、知識傳播、本土文化等各種因素聯繫起來。施賓格在無知學的解釋框架和性別視野下,勾勒出殖民地植物學別樣的歷史圖景。另外,誠如作者所言:“歐洲人關於墮胎藥的‘無知學’指的是他們不想接受殖民地收集到的知識,源自‘誰應該控制女性生育’的長期抗爭。”(280頁)在新大陸藥物傳播的另一端——歐洲,異國墮胎知識傳播中斷所造成的無知也限制了歐洲女性的生育和職業自由,被打造成父權制下完美的“家庭天使”。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