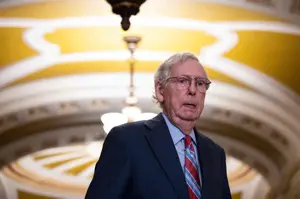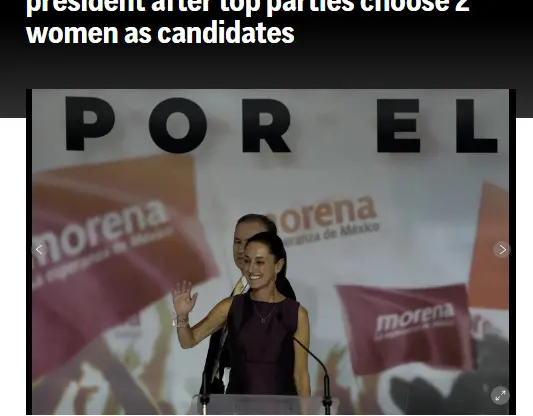魯迅,大文學家,這是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命題。然而,成爲一名作家,投身藝術創作,卻不在周樹人的規劃和理想之內。從周樹人到魯迅,這個過程似乎他自己也不曾把握。經歷了20年代種種糾紛、爭鬥與攻擊的魯迅於1932年在《自選集》自序中寫道:“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隱退,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20年代,“問題與主義之爭”愈演愈烈,《新青年》遷往南方,魯迅失去了陣地與同仁。上一次發生類似的事還是在1907年的東京。當時,他同周作人、許壽裳等人籌辦《新生》雜誌,整個計劃卻因供稿人的“隱去”和“資本的逃走”而夭折,此後便是《吶喊》自序中所說的“未嘗經驗的無聊”。
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於魯迅而言,文藝始終是要“爲人生”而非“爲藝術”的,棄醫從文旨在改變國人的精神,文藝只是一種手段途徑。故而,僅僅從“作家”這個身份來理解魯迅,可能會誤解和窄化其思想行動,以及他作爲中國文人、知識分子20世紀以來精神領袖的重要性和啓示。周樹人成爲魯迅,不只是在發表《狂人日記》時取了個筆名那麼簡單。經過近三十年的醞釀、收集和考據,北京魯迅博物館前副館長陳漱渝、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姜異新將魯迅讀過的百餘篇小說彙編爲《他山之石》出版。值魯迅誕辰140年之際,他們同劉春勇、宋聲泉兩位文學學者從這本書出發,探討了魯迅的閱讀史及其背後的思想變化,以此來理解周樹人爲什麼會成爲魯迅。

活動現場合照 出版方供圖
把魯迅放到“世界文學的大環流”中去審視
《他山之石》分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俄國小說,第二、三部分是周氏兄弟所譯《域外小說集》白話文版,第四部分爲其他零散篇目。翻開《他山之石》的目錄,魯迅讀過的作家中有很多是當代大衆所熟悉的,例如普希金、契訶夫、莫泊桑、夏目漱石。何以耗時三十年來編定這份書單呢?在很大程度上與魯迅接觸這些小說的方式有關。
魯迅接觸現代小說,基本是去日本留學後的事。據陳漱渝介紹,日本當時有一套刊物叫《小說譯叢》,刊載日文轉譯的外國小說,魯迅在東京時從中選了十來篇俄國小說做成簡報,他的俄國文學之旅是以日語爲中介開始的。日本明治時期譯介了大量外國文學,但翻譯大多粗疏,對情節有刪改增減,有時甚至會把作者的國籍弄錯,小說標題也經常擅自改動,例如屠格涅夫的一篇小說因女主角漂亮,愛賣弄風情,被改名爲《妖婦傳》,而一篇叫作《宿命論者》的小說其實是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一節。陳漱渝表示,想要弄清這些日譯俄國小說到底是什麼、當時用的何種版本,不是一件易事,再請俄文專家來翻譯,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就過去了,這當中,將《域外小說集》轉爲白話文又是一項工作。
宋聲泉認爲,《他山之石》解釋了《狂人日記》的橫空出世,也揭示了魯迅現代小說素養的來源,“如果翻翻當時中國最火的出版物,像《小說月報》《小說叢報》一類的,你會發現上面的文字和《狂人日記》相差太大了。”這與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己“看短篇小說卻不少”以及“‘小說作法’之類的一部都沒有看過”一致。她還指出,日譯俄國小說部分爲我們研究魯迅和外國小說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過去總愛講魯迅與某國文學如何如何,但考慮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其實更應該把魯迅放到“世界文學的大環流”中去,比如說看俄國文學是怎麼到日本的、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如何接受它、又如何把它變爲中國的、法國文學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是什麼樣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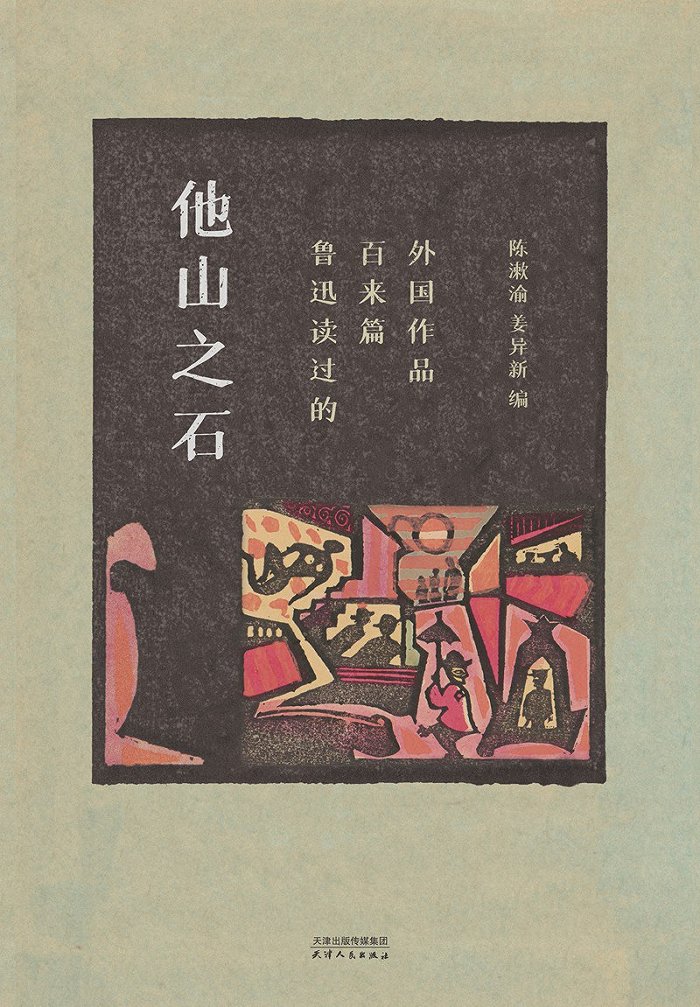
《他山之石》 陳漱渝 姜異新 編 領讀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8
夜晚與文學家魯迅的誕生:“沒有餘裕就沒有選擇的可能”
毛澤東給魯迅定了三個身份——“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中學教科書裏的魯迅只通過小說文章來承擔這三個身份,比如論及魯迅和小說的關係,大多以《狂人日記》的發表爲起點,語文教學對魯迅生平的介紹還不是很多,很合魯迅說的“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但正如劉春勇所說,魯迅最早從事小說事業是從翻譯開始的,“他一輩子都在翻譯,成爲小說家之前在翻譯,臨終前不寫小說了,但他還在翻譯果戈裏的《死魂靈》”。
“魯迅成爲一個小說家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劉春勇說道。他認爲,魯迅受梁啓超“小說與羣治”說影響極大。梁啓超在《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將小說視爲啓蒙的工具,可以用來喚醒國民覺悟。仙台時期,親歷日俄戰爭下中國人的侷促與麻木後,魯迅轉身投向文藝中尋求的正是叫喊與反抗,自然傾向於看俄國、波蘭、印度等地的作品。投身文藝活動失敗後雖對啓蒙抱以冷的態度,卻絕不抹殺砸壞鐵屋的希望,因而纔會應了朋友們的囑託,爲《新青年》撰“小說模樣的文章”十餘篇,集爲《吶喊》。
仙台時期對魯迅的重要性往往歸結到《藤野先生》中所寫的幻燈片事件,姜異新補充了這一時期的另一重要性。即日俄戰爭中,不單是中國人的反應直接促使魯迅意識到“如不改造精神,強健肉體亦無用”,戰爭本身也促使魯迅通過文學來了解這些國家。在此過程中,“他反而獲得一種藝術的愉悅感、一種心靈的溝通”,因此決心返回東京去閱讀世界。東京三年,魯迅花了很大功夫讀小說、翻譯小說,他和周作人的翻譯工作甚至引起了日本文化界的關注。
在活動最後談到周樹人何以成爲魯迅的時候,宋聲泉特別提到了魯迅說的“餘裕心”。她認爲,談魯迅的誕生繞不開夜晚,假使魯迅正兒八經地在東京德文學校唸書拿學位,很難想象中國的現代文學會如何,因爲魯迅是個愛夜的人,他的作品中多次寫到夜晚。據周作人回憶,他也是個在夜裏下苦功的人,可以說魯迅成爲文學家的過程是在夜裏完成的。“沒有餘裕就沒有選擇的可能,”宋聲泉說道。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