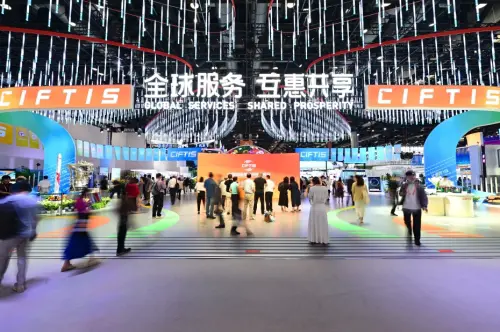蘭德爾·賈雷爾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學生時代正值美國大蕭條時期,隨後又經歷了二戰。入伍參軍的經歷爲賈雷爾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他也因書寫簡明有力、充滿人性關懷的戰爭詩確立了在詩壇中的地位。與此同時,賈雷爾還是一位文筆辛辣、富於洞察力的評論家,被譽爲“繼艾略特之後美國最重要的詩人批評家”。羅伯特·弗羅斯特、W·H·奧登、伊麗莎白·畢肖普、瑪麗安·摩爾、羅伯特·洛威爾等著名詩人都得益於他的推崇。
賈雷爾的詩歌創作始於大學期間,他曾師從評論家羅伯特·佩恩·沃倫和詩人艾倫·塔特,這兩人也成爲了他走上文學之路的引路人。當戰爭來臨的時候,賈雷爾已經擁有了豐富的詩歌詞彙和對形式的掌握。194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給一個陌生人的血》,同年,他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成爲一名飛行員教練,不久後又擔任導航塔操作員。戰爭帶來的巨大沖擊使賈雷爾的詩歌變得鮮明而緊湊,他的戰爭詩往往以生動的細節爲基礎,富有戲劇張力。另一方面,他也將自己敏銳的感觸和對戰爭的批判注入詩中,揭示出戰爭不可避免地把人變成了動物或工具。
《球形炮塔炮手之死》是賈雷爾的戰爭詩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首。詩中提到的球形炮塔從外觀上看是一個有機玻璃的球體,通常被置於一架B-17或B-24轟炸機的腹部,可容納兩架機關槍和一個矮小的炮手。與其他單純描繪戰鬥場面的詩不同,賈雷爾在詩中以炮手的視角,將在球形炮塔中追蹤敵方的感受比作胎兒蜷縮在子宮裏,“生命的降臨”也因此如同一個蘊含死亡意味的夢,凸顯出生命在戰爭中的虛幻與無常。
二戰後,賈雷爾不再書寫戰爭詩,但主題依然與命運、夢境、孤獨與死亡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非戰爭詩中,賈雷爾也常常以同情的目光注視他筆下的人物,尤其願意站在女性和兒童的處境去思考他們的命運。他的詩集《華盛頓動物園裏的女人》獲得了1961年美國國家圖書獎,他還曾著有多部兒童小說。
日前出版的中譯本《賈雷爾詩選》集結了賈雷爾幾部重要詩集的精選作品。這部詩選最初於1955年問世,由詩人親自編選,充分展現了詩人擅長刻畫場面、營造情境、表現人物夢境和無意識等藝術特點。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中選取部分詩作,以饗讀者。

《賈雷爾詩選》 [美] 蘭德爾·賈雷爾 著 連晗生 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07
球形炮塔炮手之死
從我母親的睡眠我降落在國家中 , 我蜷縮在它的肚子直到我的溼皮衣凍結。 離地六英里,離開它生命的夢, 醒來時我看到黑色的高射炮和夢魘般的戰鬥機。 我死後,他們用一根軟管把我從炮塔衝出。
損失
不是即將死去:每個人已死去。 不是即將死去:早前,在例行的撞毀 我們已死去——我們的訓練場 打電話給報紙,寫信給我們的家人, 而比率上升,全因爲我們。 我們死在年鑑的荒誕頁面, 散佈在五十英里外的山上; 跳落在乾草堆上,和一個朋友打仗,我們 閃耀在我們從未見過的航線。 我們像姑媽、寵物或外國人一樣死去。 (當我們離開高中,沒有他物爲我們而死 以估測我們的死亡方式。)
駕着我們的新飛機,和我們的新隊員,我們轟炸了 沙漠或海岸附近的靶場, 向拖靶開火,等待我們的分數—— 然後轉爲接替隊員,然後在一天早晨 醒來,在英格蘭上空,進入激戰。 別無二致:但如果我們死去, 並非意外,而是一次失誤 (一個人人易犯的失誤)。 我們閱讀郵件,數着我們的任務—— 駕着起着女孩名的轟炸機,焚燬 在學校裏瞭解到的城市—— 直到我們的生命耗盡;我們的身體躺在 那些我們殺死而從未見過的人中。 當我們持續夠久他們給我們勳章; 當我們死時他們說:“我們的損失甚微。” 他們說:“這有地圖”;我們焚燬了城市。
不是即將死去——不,從未即將死去; 但我死的那晚,我夢見我的死, 而那些城市對我說:“你爲什麼要死? 如果你滿意,我們也滿意;但我爲什麼要死?”
哦,我的名字就叫山姆•霍爾
三個囚犯——最大個是黑人—— 而他們的一個守衛 站在排水溝上的新橋旁邊: 他們再一次聽那波段,
它的進行曲每天此時的噼啪響 來自崗哨的揚聲器。 飛機在上空嗡嗡飛過;夏天的雲朵 飄過,又消失無蹤
在他們和全體人員已征服的空氣中—— 但囚犯們仍然站着 在列隊行之後聽一小節。而後 他們在沙地上跋涉
走向那些散亂的草,蓖麻灌木叢, 和洗得發白的岩石, 對他們來說,這些代表軍隊和秩序 (儘管他們的樹枝、麻袋、
燒傷的鬆弛的臉和緩慢的走路—— 警衛正微微打着呵欠—— 都判然有別,似乎四人在打一場 他們自己的戰爭)。
有一刻他們尋找殘羹;一個吹着口哨。 當警衛開始用他 遲緩的山地口音,唱《山姆·霍爾》, 他們都停下,咧嘴而笑。
新喬治亞島
有時,當我醒來,我發呆時,星辰旁邊的 樹枝,對於我,是我的監獄柵欄; 爬蟲羣集、穿過毯子,毯子像戰爭之前 舊牢房裏的牀一樣堅硬——
在那些日子,沒吃晚飯,我在睡眠中呻吟 帶着毆打的條痕,艱難困累的舊夢 鎖鏈般覆於我的四肢;直到利用我的世界 和一年將我弄醒,此時我學會了服從。
在用合衆國刀子劃出的樹幹刻痕旁, 狗牌鏈隨風翻動;而我睡眠, 被付錢,死去,一個士兵。爲自己生命而戰者 失去它,失去它:我爲我的世界而殺戮,此刻自由了。
戰地醫院
他翻轉着,開始醒來。 一種感知到的 疼痛,困擾着他盲目的溫暖;他呻吟着, 而第一批橫穿的戰鬥機 高處掃射的突突聲 將他的睡眠搖晃成碎片,隨着 急遽下降的爆炸耙着黑暗,已經完結。 他所知道的一切
洪水般淹沒了他;但他畏懼 黑暗中彎曲的 火焰線:“大公鴨拍翼 飛向結冰的湖面—— 我的散彈槍在我的腦袋中結結巴巴。 我躺在自己的牀上,” 他低語,“做夢”;他想着醒來。 舊錯。
小屋嘎吱響着;他聽到了呻吟聲,他想 這聲音是自己的—— 而呻吟着,把縫線的、盲目的、包紮着的頭 轉向隨拂曉而變紅的 帳篷門。一個聲音說:“是的,這一個”; 他的手臂刺痛;然後,他獨自一人, 他不知道,想起——但反而 睡着了,感到舒服。
黑天鵝
當天鵝把我的姐姐變成一隻天鵝 我晚上要去湖邊,從擠牛奶的地方: 太陽會像天鵝一樣,從蘆葦叢中往外望, 一隻天鵝的紅喙;而喙會張開, 裏面有黑暗,有許多星星,還有月亮。
在外邊湖中,一個女孩會發出笑聲。 “姐姐,這是你的粥,姐姐”, 我會呼喊;而蘆葦叢低聲又絮語, “去睡吧,去睡吧,小天鵝。” 我的腿全硬了,長出了蹼,而我的翅膀
絲綢般的羽毛,像星星一樣,沉入 蕩進蘆葦叢又盪出的漣漪: 透過水的疊音和嘶嘶聲,我聽到了 有人叫“妹妹……妹妹”,在遠處的岸邊, 而當我張開喙回答的時候
我聽到我沙啞的笑聲跑到了岸上 而看到——終於看到,從湖那綠色的 低丘游出,白色石頭的天鵝們: 那白色的,有名字的天鵝們……“這都是一個夢。” 我低語着,從草褥的軟毛聽見
湖牀的疊音和嘶嘶聲。 “睡吧,小妹妹”,天鵝們都唱着歌 在湖牀的月亮、星星和青蛙那裏。 但我的天鵝姐姐叫着:“睡了吧,小妹妹。” 整晚都用黑色的翅膀,撫摸我的翅膀。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