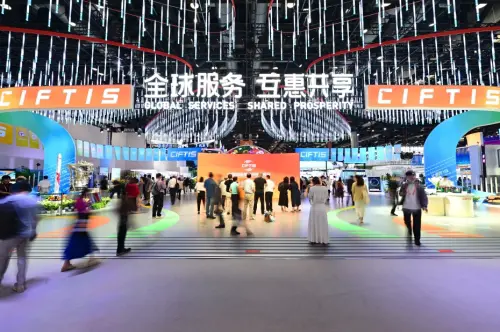“我已經習慣了不獲獎——這是我的打算,也是我的心理準備,”沉默寡言的南非小說家達蒙·加爾格特在他的第九部小說《承諾》(The Promise)獲得布克獎後的第二天早上說。他以前曾兩次入圍,憑藉2003年的《好醫生》(The Good Doctor)和2010年的《在一個陌生的房間》。他認爲整件事“令人深感不安”(他的母親已將他的詳細聯繫資料提供給南非的記者),他說前一日的頒獎典禮感覺一點也不真實,“就像被打中頭一樣。顯然,對於這本書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夜晚,所以我很難對此不滿意。”
這位57歲的作者本人身材瘦小(他是一位堅定的瑜伽修行者),談話中嚴肅而有禮貌,但小說中變幻莫測的狡猾敘述者的尖銳聲音顯然也屬於他。《承諾》通過40年來的四次葬禮,以創新的風格描述了一個南非白人家庭的故事,記錄了種族隔離後南非的衰落。這可能更像是JM·庫切的作品,而不是理查德·柯蒂斯的作品,但加爾格特的“四次葬禮”卻出人意料地有趣。(這家人被稱爲斯瓦特,在南非荷蘭語中是“黑人”的意思,正如他所說,是“一種內部黑話”。)除了《倫敦書評》最近的一篇“批評”之外,這部小說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比如一位評論家在書評開篇寫道,“令人驚訝的是,很多小說家都非常優秀,但只有少數是傑出的。”
通過一系列葬禮來講述故事的構思是在一次午餐酒後出現的,在那次午餐中,一位朋友用一系列家庭葬禮的軼事來“取悅”他:“間接吸引了我。”小說最本質的“承諾”的衝突——母親臨終前,希望她的黑人僕人薩洛米能得到她在家庭農場居住多年的小破屋——也是受到一位朋友的啓發,這位朋友的家庭和小說中的斯瓦特家一樣,“是歷史悠久的南非白人家庭風格”,想辦法不履行類似的承諾。
小說自1986年始,以2018年結尾,違背承諾的想法巧妙地貫穿始終。四場葬禮大約相隔40年,在南非近代史上也意味着四位總統。加爾格說,“和其他人一樣,對從波塔的黑暗時代到曼德拉的黃金時代運動,我感到難以置信的興奮,儘管其中總有一些不真實的意味,然後進入姆貝基時代的模糊地帶,最後來到祖馬統治時期的災難。”
他本並不打算髮表任何政治聲明,而是將國家情緒作爲故事的“背景牆紙”,將1995年的橄欖球世界盃、艾滋病毒、暴力犯罪增加和氣候變化的影響納入其中。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本小說的發展軌跡是向下的。加爾格回憶道,“我們在1994年擁有的承諾感是顯而易見的。而這種承諾幾乎已經消散了,我們現在的情況並不樂觀。”
書中幾乎所有的角色都未能實現他們的承諾,尤其是作家安東,他和作者一樣,大約同一時期在比勒陀利亞長大。“種族隔離制度的建立就是爲了服務於像安東這樣的人,”加爾格特說,“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擁有特權和權力。我認爲這種承諾對南非的白人男性來說可能已經消失了,但這並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安東超凡脫俗的妹妹阿莫爾決心確保他們母親的遺產得到尊重,他們之間的分歧反映了南非白人面臨的困境:“她的解決方案是放棄她的遺產,我想這確實是一種方式,但這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方案嗎?”他問道,“你如何能放棄你的特權?你不可能像在衣帽間那樣把它交出去。”哥哥和妹妹代表了加爾格特自己矛盾心理的兩面,在“利己主義和不厭惡權力的束縛,與放棄權力的衝動”之間糾結。
儘管充滿死亡、腐朽和失望,但寫作這部小說“非常有趣”。雖然喬伊斯、伍爾夫和福克納對他的影響很大,但費里尼也是——他還爲本書撰寫了序言。加爾格特在寫初稿時遇到了障礙,他休息了一段時間,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他向所有遭遇寫作障礙的人推薦這個做法。“語言是電影中最不重要的元素,”他說,“沒有人關心語言,這很奇怪,因爲如果你是一個小說家,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語言。”相反,他發現“攝影機的眼睛是自由的,它可以關注場景的任何地方”。
書中我們唯一沒有涉足的地方是薩洛米的內心,她對她周圍的人來說是“隱形的”,這種沉默是故意的。“像薩洛米這樣的人在現代南非仍然無法發聲,”他說,“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正是南非目前問題的核心所在。”
詹姆斯·伍德在他的《紐約客》評論中寫道,《承諾》比庫切的《恥》更悲觀,後者在1999年贏得了布克獎,作爲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暗淡寫照,受到了一些批評。在不想參與任何“悲觀主義競爭”的情況下,加爾格特確實不記得曾經對未來感到如此絕望。他認爲,新冠疫情期間的政府腐敗已經把南非“推到了未知的邊緣”,“我們習慣於政客邀功的想法,但政客在這種情況下邀功似乎是絕對的道德敗壞,我認爲這使南非在財政上破產了。”
加爾格特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他和他的家人在比勒陀利亞過着“普通的郊區生活”,他形容那裏就像是“整個種族隔離機器的神經中心——不是一個適合成長的地方”。但在他六歲時,他差點死於一種黑人兒童通常會患的淋巴瘤,這意味着直到處於昏迷狀態時他才被診斷出來。
他的康復使他成爲一個“醫學奇蹟,總是被推出去參加醫生會議等等”,他認爲這導致他在公共場所會感到焦慮。“昨晚在舞臺上,我感覺好像我又成了一個醫學標本,”他說。但他也認爲,因爲康復期間“沒有手機或視頻”,別人長達數月讀書給他聽,這使得他成了一名作家。“從我熱烈愛上了故事,到想要自己創作故事,只是短短的一步。”到了高中,他寫了兩本“非常糟糕的小說”,這成爲他的第一本小說《無罪的季節》,在他17歲時出版,“現在讓我有點尷尬。”
如今,加爾格特獨自生活在開普敦,享受着“安靜的生活”,並希望這種生活能基本不變地繼續下去。“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認爲生活有些預期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實現,但通常都不會,”他對自己的性格進行了反思。在第一部小說出版40年後贏得布克獎,並且是第三次被提名後得獎,他肯定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期許。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