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鼠疫》
偉大的小說多多少少都是危險的,作家會用一些極端的情節,若干特別的人物,來挑戰社會的欣賞和容忍度。在阿爾貝·加繆賴以打響個人品牌的《局外人》中,默爾索的“荒誕殺人”就曾令無數世人驚愕。不過,他在1947至1948年間發表的《鼠疫》卻相反,這部小說的美學追求和提出的道德判斷,兩者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作爲一個在書中往往保持沉默的主角,醫生裏厄從鼠疫的興起,一直到退潮,他都在場,在看,在思考,在行動,在抵抗,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加繆故鄉奧蘭城。
Rieu,“裏厄”,這名字聽起來像是一怔,把所有話都嚥了下去一樣。裏厄本人就是這個性。當格朗哆嗦着說“這是個瘋子”的時候,他期待裏厄附和一下,給點安慰:“是的是的,他只是瘋,並沒得病。”可裏厄的回答粉碎了這期待。殘酷的事實總要有人講的,醫生當仁不讓,我們顫抖地贊爲“奉獻”“犧牲”等的其他工作,在作爲醫生的裏厄這裏僅屬於存在意義上的人的必需。
一部小說的偉大,在於時過境遷,還總彷彿在迴應當下的事情。過去,一般都認爲《鼠疫》雖然背景設在北非,卻是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巴黎,其中有奮勇抵抗德國人的,有怯懦偷生的,有猶豫不決的,有許多人犧牲,而更多的人倖存到了解放的歡慶時刻,畢竟小說發表於二戰結束後不久,而且加繆本人也是在1940年法國投降之後,親身參與了地下抵抗運動的。然而,在埃博拉病毒近年肆虐西方的時候,這個故事就已迴歸到了它的字面意義,而今,一切終於臨頭,我們也終於能體會到書中人物的痛切掙扎了。

在書的末尾,裏厄醫生在沉思着鼠疫還會再來,因爲人們已經種下了禍根:“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俱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這些話固然可看作是在警告那些認爲戰爭已經過去而且“NeverAgain”的人,但加繆對奧蘭城歷史上的那場真實的鼠疫(發生在1849年)也做過詳細研究。在他寫於1941至1945年的筆記裏,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爲日後《鼠疫》中的種種情節做思考和準備。
笛福的《瘟疫年紀事》
生活在17至18世紀的丹尼爾·笛福,以《魯濱遜漂流記》著稱,他寫作生涯早年不寫小說,倒寫了不少政論和宣傳冊,以及一部紀實文學《瘟疫年紀事》。這個“瘟疫年”指的是倫敦的1665年。那場疫情的起因不明,只有各種傳聞,也不知病毒是如何進入倫敦的。它的傳播,有人認爲是通過呼吸,有人認爲是接觸了病人的牀褥、衣物之類。醫生對疫情完全沒有辦法,更可怕的是患者的無知,他們往往直到死時才明白自己是感染者,因而之前與其來往過的其他人都遭了無妄之災。
據說,這本書直接啓發了加繆寫《鼠疫》。
在1665年的倫敦,大多數人即便知道疫病有傳播性,也不懂得如何去防止,衛生常識是缺失的,迷信第一時間佔領了人心,將疫情歸結爲上帝的懲罰是時人很自然的思路(加繆對此種心理也很感興趣,他在1940年代初專門向牧師請教過,《鼠疫》中牧師佈道的場景寫得格外精彩),因此宿命的悲聲大作;與此同時是各種偏方的流行,有人整日口含一顆大蒜,還有人把腦袋浸在醋罈子裏。同這些怪異的現象相比,《瘟疫年紀事》中更多篇幅交給了那些讓人不忍卒讀的場景:媽媽已經沒了呼吸,嬰兒仍在她的懷裏嘬奶;父母守着幼子死去卻毫無辦法……

《瘟疫年紀事》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在高度寫實的同時,笛福還發揮了他在政論上的特長,對政府、醫生、神職人員等等的作爲做了一番分析。他揭露了神職人員的僞善,說他們自稱瞭解疫病的真相,卻是十足的騙子和丑角。在對政府和公務員的評價上,他的立論相對持平,例如他說,死亡人數絕對是被政府瞞報的了,但政府在及時處理屍體、防止病毒擴散上面是有功的。他還說道,封城、封樓這些命令在實踐中是大打了折扣的,因爲一些大樓看門人在賄賂或死亡威脅的面前放了居民出門,而居民若是對民政官員隱瞞了一些危險的實情,官員也無法察覺。
小說《鼠疫》比起《瘟疫年紀事》的最大優點,就是有人物,比如裏厄和他的至交塔魯,他們兩個人都在記錄。裏厄願做見證者,只是記錄;塔魯卻憤世嫉俗,他用諷刺的眼光來觀察人們的舉動,同時思考鼠疫之下的生活的意義。
《瘟疫年紀事》中的揪心情節,如今讀來更加揪心:公共場所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死老鼠,旅館裏、餐館裏、公交車上、民宅中,起初人們不以爲意,即使耳聞了病例也強行認定是偶然事件;後來病例漸多,各方人士又散佈消息說不會傳染,要員們總是在安撫,把有利的消息都散佈出去。再後來,人們自欺的防線塌了,封城了。人們接受了現實,一番怨念之後,坐等官方消息……鼠疫過去的時候,沒人敢輕舉妄動,就如同當舞臺黑下來,每個人都在屏息等待第一聲鼓掌,以便確認戲真的已經結束了。
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蒙德》
作爲同樣經歷過戰爭的作家,赫爾曼·黑塞也時時思考疫病的隱喻。但在他這裏,疫病作爲一種極端的處境,主要是爲了讓主人公領悟到某些超乎自身的東西而存在的。黑塞不像加繆那麼注意社會,他醉心於對個人的探索,他典型的主人公都是漫遊式的青年,在1930年後發表的《納爾齊斯與歌爾蒙德》這部長篇中,這個青年是感官主義者歌爾蒙德。他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地上四處流浪,追尋自由而有意義的人生,卻與當時正肆虐的黑死病頻繁相遇。他看到村裏堆積的屍體;他的一個女友埃萊娜,被黑死病人強姦並咬傷後死去了;他的另一個女人,猶太女人蕾貝卡,由於歐洲人把黑死病歸因爲猶太人而受到迫害。
納爾齊斯曾是歌爾蒙德在修道院的老相識,兩人亦師亦友,他安於寺院裏恬靜的學術生活。在故事的後半段,兩個人再度相遇,歌爾蒙德得知修道院裏也鬧過疫病、死過人的時候,他便追問道:在你們這裏,有沒有發生過燒死猶太人的事情?

歌爾蒙德是那種因爲所愛的人受害,才注意到疫病的人。黑塞始終在思考的是個人,因而會賦予他的主人公以某種“天選”的光環,能夠體驗一切併發出追問,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免疫”於凡人的痛苦。
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
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裏,主角的“天選”光環甚至有些無恥。三位主角都生活在霍亂肆虐的城裏,但終生不受病毒侵害。女主費爾米納和她的丈夫烏爾比諾都是上流社會的人,但和費爾米納早有書信傳情的阿里薩則是個窮小子。阿里薩一心盼着烏爾比諾讓位,然而,進入婚姻後的費爾米納一直穩穩地鑲嵌在她的身份裏,雖然感情上時有波瀾,卻也不是能乘虛而入的;而烏爾比諾,從法國學醫回來的他一直是政府要員,是全城公共醫療事務方面的一把手,負責平息霍亂。
阿里薩號稱情種,在被費爾米納拒絕後移情於各種社會女子,他有過無數情人,卻從未染上過霍亂,在馬爾克斯的暗示中,阿里薩的青春活力正是靠不知疲倦的涉獵情場來保持的。“愛情如一場霍亂”,小說上來就放出了基調,它是病,卻是萬千疾患中最爲可取的那種,甚至還能提升對真實霍亂的免疫力。阿里薩的母親發現兒子腹瀉,吐綠水,辨不清方向,還經常突然昏厥,臉色蒼白,脈搏微弱,呼吸時發出沙啞的聲音……她十分驚慌,但事實證明阿里薩害的是相思病,只是嚴重到“和霍亂病的症狀完全一樣”。

霍亂隱藏在三個主角的背後,經常露一小臉,卻從不打擾到他們。但是,烏爾比諾雖然一上任就控制住了霍亂,從而奠定了一生的榮光地位,可是到他以81歲去世的時候,書中卻明明寫道,霍亂仍然存在,當久居城裏的費爾米納難得回一趟鄉下老家,就看到滿街的霍亂病患者,“屍體在陽光的暴曬下腫脹起來,嘴裏流出白沫。”霍亂並沒有被斬草除根,只是受害者的範圍被限制在了主流社會視野之外,都是“丟卒保車”裏的“卒”。而在城中,阿里薩終於在烏爾比諾死後熬到了屬於自己的時刻,75歲的他向72歲的費爾米納寫去了情書,在他的心目中,之前找那些女人都是爲了這一刻所做的“熱身”。
馬爾克斯筆下的霍亂,由於他圍繞“愛情”的敘事而顯得很不起眼,總是被忽略,是爲了襯出阿里薩不忘初心的“偉大”。作爲對比,安分守己的(晚年有唯一一次出軌,但他馬上向太太痛哭悔罪,顯然很不適應情人這種身份)烏爾比諾醫生多少是個消極的人物,內心沒有激情,只相信現代科學與理性,相信霍亂髮生了,就要消滅它,舍此之外並沒有別的可做的事情。他對愛情不僅無感,而且輕蔑,他認爲城裏有太多的人感染了這種病,應該好好治一治。
但談論《霍亂時期的愛情》又不能只談愛情,或者激情。黑塞寫黑死病,是爲刺激主人公覺醒,這是他的關懷所在;而馬爾克斯的更大的關懷,不在於被霍亂毀掉的社會或個體。他是以一種“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態度來引入主題的,始終着意於把霍亂變成一種徹底的隱喻,不單隱喻愛情(其實是焚身慾火),更隱喻所有失控的、無節制的人的力量。馬爾克斯對阿里薩的私德並無嘲諷,反而還頗肯定他,然而,當他着手描繪貪婪而逐利的人帶給世界的後果時,霍亂就再也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比喻了。《霍亂時期的愛情》以一個令人意外的諷刺結尾:阿里薩和費爾米納登上愛之船,進行他們所謂的蜜月旅行的時候,看到了這樣一番景象:大河已經隨着五十年的濫伐森林而毀壞,阿里薩年輕時看到的參天大樹都不見了,費爾米納一直想看的原始森林裏的動物也沒有了,在河面上曬太陽的鱷魚早就被獵人殺光了,鸚鵡的啼鳴,長尾猴的叫聲,還有河灘上神奇的哺乳動物海牛,都銷聲匿跡,或者乾脆滅絕了。死魚在污水裏翻着肚子,一路漂向了大海。兩位新人看不下去了,讓船長掉頭返航,並宣佈沿路不停,放出風聲說,船上有兩個霍亂病人。毀滅了河流生態的元兇,正是阿里薩所經營的內河航運公司。
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
人是最大的病毒之源,倘若馬爾克斯還不見得明說這點,那麼若澤·薩拉馬戈做到了。葡萄牙老作家在七旬高齡,用一本《失明症漫記》震懾了他的讀者,和那些只喜歡衝着獲獎作家名頭而去的讀書人。他寫的並不是歐洲人熟悉的黑死病(鼠疫),而是一場莫名來由的“失明症”:患者眼前一片白,並且還能以目光傳染給其他人。正因其莫名來由,所以更像是天譴。
《失明症漫記》裏的重點詞眼是,隔離。《鼠疫》中的裏厄醫生第一時間提出了要對已發現的病患實施隔離,並推行申報制,這是必需的措施,患者即便感到屈辱也只能默然忍下;而《失明症漫記》裏,由於傳染方式離奇,恐慌瞬間加劇,人們的心理防線一下子就被衝破了。在薩拉馬戈筆下的這座無名城市裏,被隔離的失明者第一時間感受到被監押的恐怖。他們失去了一切保護,甚至一有任何躁動,便會被緊張的看守人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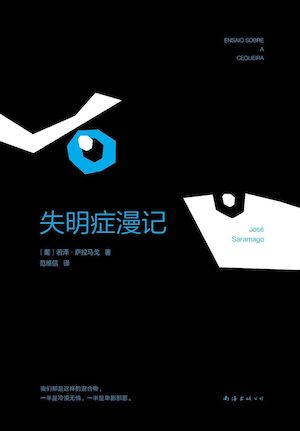
《失明症漫記》唯一讓人感到安慰的地方在於,這是小說,並非事實,然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又像是預言。那座無名城市裏的人朝朝暮暮等待好轉,可等來的卻是醫院住不下人,新患者被責令留在家中,所有正常且必要的舉措,在患者聽來都僅僅是對健全人的安撫。隔離所裏,有人藉機對其他失明者釋放心中的邪念,比如性騷擾,有人偷走公共食物,有人甚至憑着武器稱王稱霸,佔領了所有的資源,支配其他盲人。後來,失明者衝破了他們的牢籠,闖到外邊,在那些早已空無一人的公共場所裏大舉搶掠,並且肆意佔領民宅。
然而災難裏也有一些溫情的時刻,有一些希望的萌芽。比如兩位失明者——一個老人和一個年輕女子相愛了;一個走投無路的老婦人在死前打開籠門,放走了她養的兔子;還有,小說的主人公,一個失明醫生的太太,她冒充失明者進入隔離所,引着脫獄的衆盲人來到自己家,讓他們圍在一起,給他們讀書。文明在一個徹底垮掉的世界裏艱難地、一步一步地迴歸。小說中有名盲人是作家,他說,即使自己看不見,他也要摸索着寫下這段經歷。
他能寫下些什麼?薩拉馬戈一定讀過《鼠疫》,他知道“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這是加繆的想法和態度。加繆值得熱愛的理由,對我來說,就是他能在觸及事物的本質與核心的同時,仍然持有一種在人的身上“察其正”的信念。而在薩拉馬戈這裏,在醫生太太和作家的身上,我則發現了這一信念的一種較爲微弱的版本。
當《鼠疫》從寓言的設定中脫出,無限逼近人們的真實體驗時,我有了一種“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的感覺。加繆式存在主義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須以其行動,來賦予自己的存在以意義。意義,但願我們在眼下也能找到些許。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