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迪·史密斯的上一本書《大聯盟》( Grand Union )是一部富有試驗性的短篇集,然而最有趣的恰好是最不出人意料的。但這本新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暗示》( Intimations )收錄了一系列風格迥異的散文,記述了扎迪在新冠疫情期間離開紐約、來到倫敦後的封閉生活,在“一年中碎片的時間裏寫作”。她靜心冥想,探索這場大疫病對人的創造力有何影響,又如何塑造了政治輿論——與一些言語修辭上更爲冒險的東西相比,美國如何從戰後的英國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身上汲取經驗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她受到一系列影響,堪稱奇怪,比如說家庭、穆罕默德·阿里和一些 “偶發事件”,這也造就了史密斯萬花筒似的的個人形象,以及她的行文風格——將新冠病毒看作種族歧視的隱喻,順帶將英國首相智囊多米尼克·卡明斯(堅定脫歐派,提出英國羣體免疫)比作單膝跪在喬治·弗洛伊德脖頸處的美國警官警官德雷克·喬文。
這些文章的語言基調各異。有的章節把這一疫情時刻呼作“全球陷入大麻煩的黎明”,有些則認爲今天正是“全世界步入謙遜的前夕”。史密斯的文風是高傲的,她在書中寫道,“美國很少在哲學上把生存看作一個整體,”這也讓她的敘述顯得不那麼令人信服。尤其是她在談論作家對掌控力的需求時曾反思道,她自認爲與“這個奇怪而令人窒息的死亡季相比”,她更爲鬱金香着迷。新常態的日常瑣事令她興致大發,比如說隔着衣袖按電梯,又例如與媽媽通過Zoom打電話時被放大的不自在感。書中一篇文章以逃離的倉皇開頭:她胡亂收拾衣物,衝向ATM機換現金,好趕在航班停飛之前帶着家人離開,來到倫敦北部朋友的小屋裏隔離。她驚人地坦率:當一位鄰居告訴她,“我們都要走這一遭的,我們所有人,共同經歷。”她回道,“是的。”但音量幾乎連自己都聽不見。她繼續前行——真相已經大白,她要逃離這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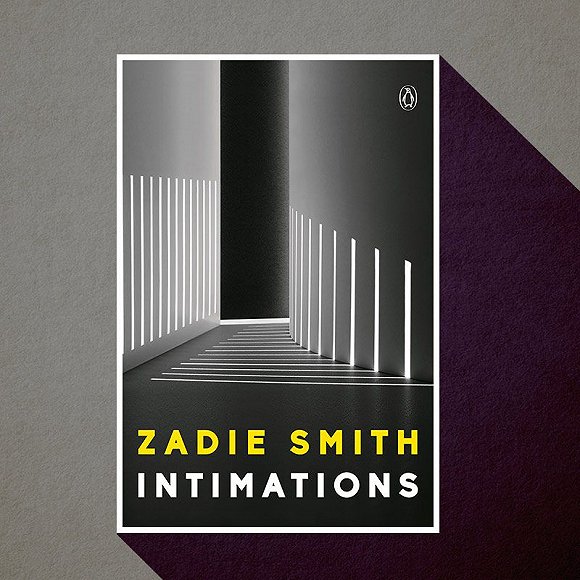
《暗示》
扎迪·史密斯認爲自己是幸運的,這種感覺領着她絮絮叨叨,貫穿全書。她略帶愧疚地描述着和按摩師在曼哈頓關於下雪天學校停課的閒聊。“他任我發牢騷,彷彿對我來說,一天不寫作就天崩地裂,經濟上、精神上等種種方面都會產生或存在主義或現實的影響。”她在書中寫道,自己之所以寫作,“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就是自己的心理怪癖,來應對我的任何個人失敗,”寫作也許可以“給認真工作的嚴肅之人帶來某種樂趣”。還有一篇文章描繪了她鄰居在隔離前創作的一副鋼筆畫:一位坐着輪椅的人在紐約客之間滑行,“這些來去匆匆的人彷彿耗子逃離一艘將沉之船。他們在逃避什麼呢?流感嗎?糟糕得多的東西我都見過了。”還有一個故事更加荒誕驚悚:史密斯弟弟同校的一個女生在隔離期間被男友謀殺,後者還放火燒了她的公寓。

左:隔離期間的我;右:隔離期間,我有六歲以下小孩的朋友
如果說史密斯因爲自己的幸運而痛苦的話,這種情緒是微妙的。在《像梅爾·吉伯遜一樣受難》中,她發出了對優勢話語的警告。這篇文章的標題取自互聯網梗,在《耶穌受難記》片場,導演梅爾·吉伯遜指揮者主演詹姆斯·卡維澤在荊棘冠下流血受苦,這張圖片成爲了表情包素材(如上圖,左:隔離期間的我;右:隔離期間,我有六歲以下小孩的朋友)。在這裏,史密斯覺得自己有義務告訴大家,“相比於許多人,她是幸運的。不方便之處自然會有,而且可以說是頻繁,但她並不因此而感到痛苦。”最終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她提出了更具挑釁性的觀點:承認自己的麻煩,會讓解決他人的困境變得更容易。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