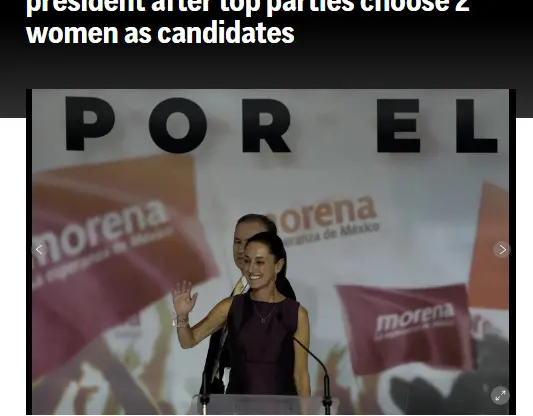在菲利普·羅斯2006年的小說《凡人》中,主人公“他”沒有一個完整的名字,他來到已故的父母墓前,偶遇了一個掘墓人,後者正在一點點雕琢新墓地的邊邊角角。主角驚訝萬分,在此之前,他一直以爲墳墓是挖掘機的傑作。兩人聊了起來,掘墓人擘兩分星地講述工作的種種細節,神情裏透着驕傲。後來主人公得知,眼前的男人正是爲他父母掘墓的人,不僅如此,很有可能下一個主顧就是自己。這位掘墓人直白的語言讓他精神抖擻,重新發現了人生終結的新意義。“我想要感謝你,”他對掘墓人說,“這是給老年人最好的一課,沒有人能比你的啓發更具體了。”
對死亡產生的超意識還往往是疾病爆發的前兆。許多講述大流行病的作品——比如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記事》、加繆的《鼠疫》和羅斯的《復仇女神》( Nemesis )——都關注到了死亡及其對生者產生的影響。羅斯在《凡人》中得出結論,如果死亡的過程能通過人的交流,層層展開,化繁爲簡,其實不失爲一種好的教育,受益者不僅是老年人。這樣的對話交流是不是一定要在一坨坨翻鬆的地表上,在散發着清新泥土氣息的空氣中,在死亡的邊緣開啓呢?實際上,配着蛋糕與茶,歡聲笑語討論死亡並不是天方夜譚,甚至更值得推崇。這就是“死亡咖啡館”背後的概念,旨在讓人們打破文化禁忌,在這個空間裏獲得一種社會特權,光明正大地探討死亡這一生命必經的體驗。
英國人鍾·安德鄔(Jon Underwood)實踐了瑞士社會學家伯納德·克瑞塔茲(Bernard Crettaz)在2010年作品《死亡咖啡館:讓死亡不再冷寂》(Cafés mortels: sortir la mort du silence)中提出的理念,不斷迭代,出現了今天的死亡咖啡館活動——非正式聚會。在這裏,除了讓人們瞭解死亡、正視死亡之外,沒有別的目的。死亡咖啡館不提供心理輔導,也不承辦悲傷的講座,更沒有什麼具體的宣傳議程。他們自稱,咖啡館的目標,只是簡單地“提高人們對死亡的認識,從而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
死亡咖啡館活動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受歡迎並不是一件奇事。即便是新冠疫情之前,各國政府就已經面臨着人口特徵變化帶來的社會挑戰。流行病學趨勢表明,現代人死亡年齡更晚,而且年老垂死的狀態持續更久。內奧米·理查茲(Naomi Richards)博士曾在2018年聯手惠康基金會第一次對死亡咖啡館進行了全球性的研究。理查茲表示,“政府和決策者都必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以及伴隨的臨終關懷需求。”各國政府都在呼籲個體、社區和機構不同層面的積極準備。理查茲認爲,“死亡咖啡館的概念似乎與許多國家的官方政策形成了共振,鼓勵通過對話幫助人們更好地規劃死亡。”

死亡咖啡館活動傳單
通過交流來提高人們對死亡的認知度,這個概念已經流行起來。9年間,72個國家裏舉辦了11000次死亡咖啡館活動。理查茲的研究發現,“死亡咖啡館活動已經從英國傳播到了北美、歐洲、亞洲、南美和非洲。在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區,這些活動有的是由移民發起,有的則是由與盎格魯文化關係密切或者剛從英國返鄉的人組織的。”
隨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死亡(以及如何避免死亡)成爲了全球共同話題。可以預見,許多國家的話語會圍繞戰鬥展開——死亡率、致死率、就近避難、封鎖。社會成爲了戰場:醫院是前線,家庭是我們避難的戰壕和散兵坑。這場戰鬥中有着明顯的勝者和輸家——勝利意味着確診新增人數曲線拉平,規避死亡,最終目標始終是零死亡。然而,要求整個社會實現都實現這一目標不切實際的,即便是“已經根除”的疾病,零死亡率也是不可能的——2019年,疫苗引起和野病毒導致的脊髓灰質炎共有500例,而鼠疫每年都要奪走650多條生命。一味追求避免死亡、忽略對話,只能進一步加劇死亡對生活的影響。
避談死亡和否認死亡的現實幾乎沒有區別。文化考古學家厄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警告說,“(無視死亡)主張了人們對貪慾和權力的追求,在社會秩序的中心埋下了非人道的種子。”貝克爾認爲,這種忽視帶來的後果不只有拖延症,還讓那些有利可圖的醫療公司和個人趁虛而入,掌控了人們死亡的方式,以及對“好的”死亡的想象。名牌棺材、葬禮套餐和臨終在牀邊提供指導的醫生都是其產生的副作用,這也正是死亡咖啡館活動試圖消解的。
死亡咖啡館活動搬到線上究竟效用如何,還有人抱着懷疑態度。格拉斯哥大學臨終研究小組的研究員索爾韋加·齊百特(Solveiga Zibaite)指出,一次成功的死亡咖啡館活動的必要因素,諸如自由流動、公開討論的空間,在線上環境可能很難實現。但線上死亡咖啡館依然十分重要,填補着我們疫病流行時的裂隙,讓我們重拾死亡的主權。

死亡咖啡館活動現場
隨着技術進步,我們對難以避免的結果的掌控力越來越強了。沒有人喜歡死亡,特別是感染新冠,在親人兩隔的痛苦中死去。但這是難以避免的,即便技術再怎麼發展,也難以逾越這一障礙。新冠疫情提高了我們對死亡和生命脆弱性的集體認識,但也讓我們更珍惜生命,渴望克服這一不可避免的魔咒。儘管我們每天都在刷新着搖擺不定的統計表,看到死亡率數字和死亡人數,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都沒有做好面對死亡的準備。我們忽視死亡,或者將其視作敵人,從而將其病態化,成爲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口中的“啃噬我們日常快樂源泉的蠕蟲”。
理查茲認爲,我們的社會終究還是有可能實現死亡咖啡館活動在過去近十年中所倡導的概念。“從文化上入手,嘗試引發人們對主流健康保障機制之外的死亡產生共鳴,這種努力最終承受着巨大的趨同壓力。這樣的文化干預可以同時存在於主流衛生體制中,也可以保留在其外。”
在理查茲看來,死亡咖啡館是一個“談話革命”,點燃了人們的希望——這個社會可以開始重視死亡主權的集體需求,並且有所行動了。通過公開對話,也許我們可以消除對死亡的病態仇視,並且認識到,接納死亡並不等於鼓勵赴死。
古往今來,死亡這種既普通又因人而異的經歷都深埋在人們的情感中。從十五世紀的道德劇《世人》(Everyman)中,我們找到了英語戲劇中最矚目的臺詞之一:“噢,死亡,當我最不經意的時候,你悄然來訪。”死亡咖啡館活動的主旨是減輕死亡的驚嚇,通過交談,讓死亡禁忌轉變爲一種人生體驗。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