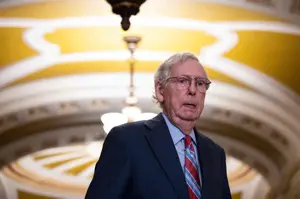凱瑟琳·瓦伊納: 你好,娜歐米。你在居家隔離這段時間過得如何?
娜歐米·克萊因: 對於那些像我一樣通過Zoom教學生的人來說——在家上課,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研究烘焙,我們真的很輕鬆。現在我回到加拿大和家人一起過暑假。在加拿大,如果你來自美國,將會被嚴格隔離。我差不多有兩個星期沒出門了,如今其實對結束隔離有些恐懼。
凱瑟琳·瓦伊納: 在你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句來自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名言:“人類纔是生物危害,機器不是。”這句話讓我毛骨悚然,對未來感到恐懼。你那篇關於“屏幕新政”(Screen New Deal)的文章很有趣。
娜歐米·克萊因: 早在新冠病毒之前,硅谷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計劃,設想通過科學技術替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因此,在科技尚未完全替代的人與人接觸的某些領域,有一個計劃——用遠程學習代替面對面教學,用遠程醫療代替面對面醫療,用機器人代替面對面分娩。在後新冠時代,所有這些計劃都作爲一種技術被重新包裝,來解決人與人接觸的問題。
然而,在個人層面,我們最懷念的反而是人與人的接觸。所以我們需要擴大與新冠共處的選擇範圍,但我們還沒有疫苗。即使有了突破,也需要很多很多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才能達到我們需要的規模。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一切呢?如果無法維持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會接受前新冠時代的“正常生活”到如今的改變嗎?我們會允許孩子通過遠程科技來學習嗎?還是我們要更加註重投資於人?
與其把我們所有的錢都投入到“屏幕新政”中,並試圖用降低我們生活質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我們爲什麼不能聘請更多教師呢?爲什麼我們的教師人數不能增加一倍,教室規模縮小一半?爲什麼我們不能想辦法進行戶外教育呢?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來思考如何應對這場危機,但並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我們必須回到前新冠時代的生活。這樣只會更糟,只會有更多的監控、更多的屏幕和更少的人際交往。

2019年,在利茲市的一場抗議活動中,環保運動反抗滅絕的支持者們在進行抗議活動。圖片來源:Photograph: Ian Forsyth/Getty Images
凱瑟琳·瓦伊納: 你認爲政府會支持這種說法嗎?
娜歐米·克萊因: 我最近聽說新西蘭總理傑辛達·阿德恩倡導每週工作四天,以重建新冠肺炎後的新西蘭。新西蘭是一個非常依賴旅遊業的國家,但新西蘭的新冠死亡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卻要低得多。新西蘭不能像過去那樣對遊客敞開大門,所以有人認爲新西蘭人應該少工作,少拿工資,多享受休閒時間,在自己的國家安全地享受。
我們應該如何放慢腳步?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感覺就像每次我們踩下標有“一切正常”或“恢復正常”的加速器,病毒就會捲土重來,讓我們“慢下來”。
凱瑟琳·瓦伊納: 我們都喜歡慢下來的時刻,但不管發生什麼,英國政府都堅決要回歸正常生活。所有的店鋪都開張了,酒吧都開張了,我們迫不及待地想去度假。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是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
娜歐米·克萊因: 這太瘋狂了。想要敞開大門的人只佔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事實上,大多數人更關心的是在一切安全之後重返工作崗位,在安全之後送孩子上學。政府有時框定給人們想要的東西,但這不是民衆真正想要的。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處理方式與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處理方式有相似之處。他們正在把對抗病毒變成一種測試男子氣概的遊戲,即便在鮑里斯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後依然如此。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談到,他是一名運動員,所以他知道如何應對新冠(巴西總統在接受採訪後不久就透露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特朗普則說他靠的是自己的好基因。
凱瑟琳·瓦伊納: 在喬治·弗洛伊德死後爆發了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你對此有什麼看法呢?這件事相當新奇,在新冠病毒的危機中,世界各地都在爆發反對種族主義的大遊行。
娜歐米·克萊因: 這種反對種族主義的抗議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認爲這一次的抗議在某些方面是獨特的,因爲在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新冠病毒對非裔美國人的影響巨大。據統計,在美國70%死於新冠病毒的是非裔美國人。
無論是因爲非裔美國人從事危險工作、沒有得到保護,還是因爲遺留下來的社區環境污染、壓力、創傷、不安全的工作場所和歧視性的醫療保健。黑人社區正承受着高額的病毒致死風險,這與我們同甘共苦的想法背道而馳。阿哈邁德·阿貝里、喬治·弗洛伊德、布倫娜·泰勒等人的遇害,在這一深刻創傷的時刻,更讓人受到極大觸動。
但還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都在問,那些黑人之外的人在抗議活動中做什麼?當然對於這種抗議規模而言,很多東西都是新的。許多這樣的示威是多種族的,黑人領導的多種族示威。但爲什麼這次會有所不同?
我有一些想法。一是新冠病毒流行給我們的文化注入了一些溫和的思考——當你慢下來的時候,才能真正地感受事物;而當你處於持續的激烈競爭中,你就沒有多少時間去移情思考了。從一開始,病毒就迫使我們思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你首先想到的是,我和別人共同觸摸的東西是什麼?是我吃的食物,是剛送到的包裹,是貨架上的食物——但資本主義恰恰讓我們忽略了這些聯繫。
我認爲,強迫我們以相互關聯的方式思考,可能促使我們中更多的人開始思考這些種族主義暴行,而不會單純認爲這是別人的問題。

《着火》
凱瑟琳·瓦伊納: 在你的新書《着火》( On Fire )的新序言中有一句話我很喜歡,你說,“當災禍升級到無法忍受之前,一切都是糟糕的。”而警察對待黑人的方式就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情況。
娜歐米·克萊因: 每當災難襲來時,總會有這樣的言論:“氣候變化不會歧視我們,流行病也不會歧視我們,我們都身處其中。”但事實並非如此。災難往往有着放大鏡的作用。如果你之前在亞馬遜的倉庫染上了病,或者如果你長期接受護理和看護,生活已經失去價值,這些東西如今都會被放大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如果你之前只是可以替代的,那麼現在就是可以被犧牲的。
當然我們現在討論的只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暴力。其實還有很多隱藏的暴力,那就是家庭暴力。說白了,當男人有壓力的時候,女人和孩子都會有壓力。這種隔離會讓人壓力很大,因爲即使是最親密的家人往往也需要一些相對獨立的空間。還有裁員導致的經濟壓力。現如今,種種壓力之下的女性處境真的非常糟糕。
本文采訪者凱瑟琳·瓦伊納是《衛報》總編輯。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