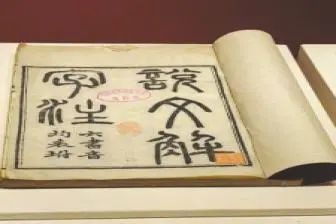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不僅僅是老年人,年輕人也會得新冠!”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教授、老年病學專家Louise Aronson發現,人們在社交網絡上用這樣的句子呼籲大家重視新冠疫情。她在3月22日於《紐約時報》撰文批評稱,這種說法的潛臺詞似乎是:如果只有老年人會得新冠,那麼疫情就不怎麼重要了。
今年2月,中國國家衛健委和世衛組織指出,新冠肺炎病毒幾乎人人易感,患者感染後多數爲輕症病可痊癒,重症和死亡高危人羣爲年齡60歲以上以及患有基礎性疾病者。此外,在分析意大利死亡率高的情況時,《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的老年人新冠死亡率特別高,死亡者大多數是70歲以上和患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年輕人把新冠病毒稱爲“老人消滅者”(Boomer Remover),“#BoomerRemover”的標籤一度也在推特上成爲熱門話題。 “Boomer”一詞在西方常被用來指二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如今已經年長的人。
新冠死亡率特別高的老年羣體不僅成爲了年輕人的嘲弄對象,而且還很可能是第一批被放棄的人——在3月9日意大利全境封鎖之後,意大利麻醉-鎮痛-復甦-重症監護學院(SIAARTI)就疫情發佈的針對醫務工作者的指導手冊提到,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可能不得不面對道德選擇,即放棄治癒希望較低、治癒後繼續存活年數較少的病人,優先救治年輕人,具體做法包括“爲重症監護設置年齡上限”。手冊撰寫團隊說,希望這條建議永遠不會被用上。
戰勝新冠需要以犧牲老年人爲代價嗎?《名利場》一篇標題爲《德克薩斯副州長丹·帕特里克:當爺爺的人應該自願爲經濟去死》的文章報道了丹·帕特里克對此的看法,在丹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稱,隨着新冠病毒疫情打擊美國經濟並導致企業關閉,像他這樣的老年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保護孫輩的經濟。“沒有人問我,作爲一個老年公民,你願意用你的生命作代價,換取爲你的子孫後代保住所有美國人都愛的這個國家嗎? 如果這就是交換,我願意。”

70歲的德克薩斯副州長丹·帕特里克
犧牲老年人以拯救年輕人和未來的看法在此次疫情中並不鮮見,烏克蘭衛生部部長伊利亞·葉梅茨在一次採訪中將65歲以上的老人比作“屍體”,直言“我們應該算一算,要把多少錢花在活人身上,而不是屍體上”,引起輿論風波,隨後伊利亞·葉梅茨辭職。
這種觀點無疑會引發爭議,但其背後拋出的疑問是:當資源有限時,究竟如何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把過多資源偏向老年人的話,年輕人的資源則會相對變少,而青壯年纔是構成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如果沒有青壯年,那麼社會就會缺乏活力,經濟會衰退,接着財政稅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也會受到限制。這或許是丹·帕特里克的認識。但是,把過多的資源用於年輕人,會忽視對老年人的關懷,將心比心,包括你我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度過悽慘的晚年。
衛生保健中的年齡歧視
Louise Aronson認爲,不重視新冠的最大受害者老年人羣體,這種態度是典型的年齡歧視(ageism)。所謂年齡歧視,指的是根據年齡上的差別對人的能力和地位做出貶低評價,是以年齡爲依據對個人或某個羣體做出的負面價值判斷。年齡歧視最早是美國學者羅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在1969年提出的,專門指針對老年人或者年長者的歧視。西方社會老年學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最早集中在就業領域,即因爲年齡原因無法平等獲得就業機會——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爲在就業領域,中國人已經習慣了35歲、50歲等年齡歧視門檻。而如今,新冠疫情體現的年齡歧視主要集中在衛生保健領域。
在疫情期間,年輕人把新冠病毒稱爲“老人消滅者”。《年齡歧視與老年人虐待問題研究》一書中,作者姜向羣看到,在平時的公共生活中,美國年輕人也往往會抱怨老年人:“美國老年人口占全國總數的11%,但佔去國家財政預算的25%。”這些年輕人忽視老年人過去的貢獻,抱怨老年人佔了青年人的便宜。似乎,老年人退休以後,就成了二等公民,成了社會的負擔。“失敗者”“純消費者”“一無是處的人”之類的貶義話語常常被用來形容老年人。約翰·W.羅和羅伯特·L.卡恩在《成功老齡化》一書裏也指出了美國語言當中體現的年齡歧視,其中一些格言的潛臺詞對衛生保健來說非常危險:例如,對健康問題的消極接受,認爲它們不可能被成功解決(To be old is to be sick,人老就要生病);老年人不能也不願意給他們的生活製造積極的健康變化(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老狗學不了新把戲);時間對於身心的損耗是不可避免的(The horse is out of the barn,爲時已晚)。
在新冠疫情到來時,當我們看到一些老年人自己也認同老年人負面角色認定(伊利亞·葉梅茨64歲)的時候,不免感到驚訝。歧視老年人的角色認同也是通過社會互動學習而來的。社會或者家庭成員認爲老人衰老、無用的話,老年人也會逐漸接受這種角色認定。
Louise Aronson於3月28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稱,她看到,人們把新冠疫情中老年人大量死去的原因歸咎於年齡本身,但是實際上問題在於衛生系統是存在固有缺陷的。美國醫療體制內的年齡偏見根深蒂固、無處不在,甚至在教育、研究以及最基礎的規程、結構、政策中都留下了烙印。作者舉例稱,醫學院往往會花費數月時間爲學生講授兒童生理學和相關疾病知識,花費在成年人疾病領域的是數年,可在老年病領域只有幾個星期。老年病學甚至不在必修課程表上。美國衛生研究院1986年就要求將女性和有色人種納入醫學研究範圍,卻直到33年後的2019年纔對老年羣體採取同等措施。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最大化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分配正義問題
SIAARTI此前發佈的文件似乎進一步坐實了“年齡歧視”的說法。文件提出要優先處理從其病史、併發症(其餘健康問題)及康復可能性而言“最有可能成功療愈”的病人。透過聚焦“存活可能性更大以及可挽救的生命年限更長者”,這些原則將“最大化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然而,這種做法也被解讀爲“放棄老年人”。
這種做法涉及到分配正義的問題。丹尼爾斯(Norman Daniels)在1985年出版的《醫療公正論》當中提出了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即老年人在用高科技延長自己垂垂暮已的生命,而婦女小孩等年輕人的醫療保健卻得不到合理的關注。他看到,大量的醫療資源花費在人們生命的晚期,其中美國有約30%的醫療資源消耗在病人臨終之前的六個月時間裏。丹尼爾斯認爲首先應該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達到一般壽命,這個機會比用大量的醫療資源讓一小部分人活得更長要更加道德。他提出,當病人超過75歲的時候,我們有理由限制挽救生命的醫療資源的使用。這個結論來源於他的一個合理假設,即大多數人在75歲時已經實現了自己的人生計劃。75歲也是當時發達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這樣,當人們到達這一年齡以後,就有合理的理由撤銷昂貴的生命維持治療。
老年人常常花掉社會大部分醫療資源,雖然他們可能僅僅佔據社會總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隨着全球老齡化的來臨,老年人花費的醫療資源會逐漸增多。在有些發達國家,65歲以上老人在衛生保健上的消費超過了所有65歲以下人口的總消費。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究竟給老人多少醫療資源是恰當的?
《衛生保健的分配正義研究》一書中,作者李紅文提到,在關於以年齡爲基礎的衛生保健分配問題上,阿蘭·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與丹尼爾斯有類似看法:由於老年人已經活了很多年,按照公平的原則,年輕人應該在延長生命的醫學治療上享有優先性。這一論證的基礎是,每個人都應該享有正常的生命年限,沒有活到正常年歲的人是被欺騙的,而那些超過了正常年限的人則借了他人的時間。威廉姆斯認爲,代際公平不僅僅是允許,而是要求對老年人實行更大的區別對待。丹尼爾·卡拉漢(Daniel Callahan)則認爲,社會應該幫助老年人度過一個完整而自然的生命期限,也就是80歲左右,他認爲在這個時候,生活的可能性總體來說已經實現了,在這個年齡之後死亡是一個相對可以接受的事件。醫學應該盡力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而不是一味地尋求延長生命的方法。如果資源有限,社會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作出選擇時,應該把資源集中在延續年輕人的生命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質量上。
類似的,在《牛津通識讀本:醫學倫理》當中,作者託尼·霍普認爲,決策的核心原則是,我們所做的決定應當全面將所獲得的的壽命年份最大化。一個衛生保健體系爲救少數人而讓多數人死去是否正確,這是有疑問的。作者看到,任何一個衛生保健體系在對延長人的生命做決定的時候,都必須延長一些人的生命,以犧牲另一些人的生命作爲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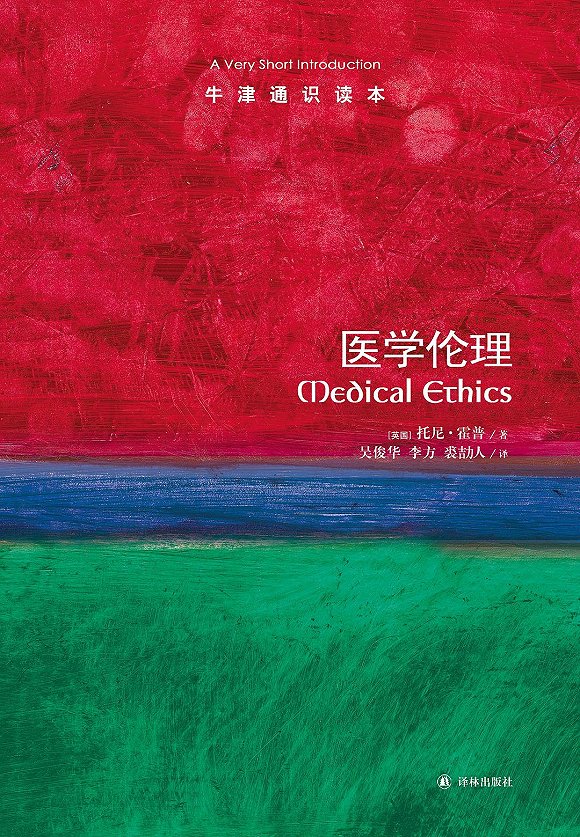
[英國]託尼·霍普 著 吳俊華 李方 裘劼人 譯 譯林出版社 2015-9
可是,人們真的能夠接受這樣的結論嗎?每一代的老年人都會覺得,在人生的早期自己並沒有享受什麼高新醫療服務,而這些技術是用包括自己在內的納稅人的錢發展起來的。而現在自己老了,被拒絕使用這些技術顯然是不公平的。
功利主義與人道主義
SIAARTI“最大化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做法是符合功利主義倫理的。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認爲,“每個(人)都算一個,沒有(人)多於一個,”每個個體的利益都應當予以同樣程度的關懷,沒有誰的快樂比其他人的快樂更重要。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爲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最正確的行爲是將效益達到最大。效益就是快樂,傾向得到最大快樂、避免痛苦就是正確。《牛津通識讀本:醫學倫理》的作者託尼·霍普也稱自己“樂於認同最大化壽命年份的總數”,“對收益最大化的做法有偏愛”。但是,他也同時看到,他其實是一個少數派,因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衛生保健體系採用的是這種方式。
在實際操作當中,許多人反對最大化壽命年份的做法。人們的直觀訴求是,爲少數人提供大的收益(延續如果不接受治療就會死去的人的生命)比爲多數人提供微不足道的收益(過早死亡率的微小降低)要好。爲什麼呢?以《拯救大兵瑞恩》爲例,我們不妨反思一下,真的應該用許多生命去冒險換回一條生命嗎?可是在電影裏,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會覺得拯救計劃是錯誤的。同樣的道理,一個社會在老年人身上花費高額的衛生保健費用也是對的。社會怎麼可以對老年人說:我們現在要犧牲你,拿這些資源去救更多年輕人。我們又怎麼能把這種話講給他們悲痛的親人呢?
當年輕人把新冠病毒稱爲“老人消滅者”的時候,當人們做好準備犧牲老年人生命的時候,如果這位要被“消滅”的老年人就在我們眼前,我們熟知他/她的人生經歷、痛苦與歡笑、挫折和夢想,我們會怎麼說?如果這個要被犧牲的老年人恰好是我們的祖父母,那我們又會怎麼說?我們的人道主義精神和道德想象力被喚醒了。當然同時,我們的道德想象力也必須清醒地面對那些因爲沒有足夠資源而得不到拯救的年輕人。也正因如此,SIAARTI文件才強調稱,僅向部分病人提供健保資源的做法,唯有在窮盡一切手段來開源,或將病人轉移到資源充足的地點後纔是有辯護的。因爲,我們不能夠陷入把人的生命看作一種客觀物體看待的純功利觀點,應該履行對病人健康的道德責任和道德良心,但同時,人道主義也必須顧及他人和社會的利益。
正如託尼·霍普所言,死亡並不會因爲我們不能把一個面孔和一個本可以被挽救的人對上號而變得不重要。不論怎樣,我們必須防止自己把死亡看作是數字,看作是統計學上的死亡。因爲,每一個死亡背後都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們的親人、朋友,也和我們一樣,是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