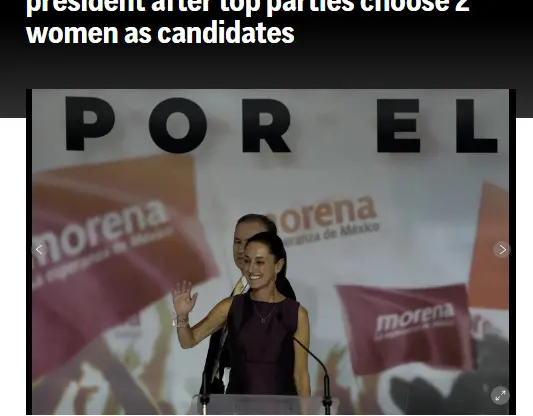在過去的十年中,從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到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班,妖魔化移民已成爲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關鍵部分。與此同時,隨着內戰的加劇和氣候變化影響的出現,人們可能需要離開故土的原因變得越來越值得關注。作家兼新聞記者蘇克圖·邁耶塔(Suketu Mehta)在他的著作《這是我們的土地:一份移民宣言》( This Land Is Our Land: An Immigrant's Manifesto ,Jonathan Cape出版)中指出,只有事實和令人信服的人性故事才能與強大的民粹主義反移民言論相抗衡。
爲什麼決定寫這本書?
邁耶塔: 我本人是移民,我從未見過移民像現在這樣被妖魔化。在我寫作《極限之城》( Maximum City )之後,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寫一本關於紐約的書。然後,我花了一些時間寫完《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本書,因爲我認爲,在全世界範圍內,目前迫切需要探討與移民相關的問題。在諸如美國這樣的地方,關於移民的話語現在甚至已經開始煽動種族滅絕。
當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談論移民時,(甚至在自由派人士中)他們喜歡用這類語言:我們應該允許多少移民進入?但我想問的是:首先,人們爲什麼要移民?不是因爲他們厭惡自己的故土或家鄉,而是因爲他們的前途被富裕的國家——通過殖民主義、公司殖民主義、戰爭和氣候變化——竊取了。
能否展開闡釋一下殖民主義在其中的角色?
邁耶塔: 這本書始於祖父過去告訴我的一件軼事。他在印度長大,然後在英國殖民時期的肯尼亞工作,後來在倫敦退休。有一天,一位憤怒的英國紳士走向他,朝他(厭惡地)擺擺手指並說,“你爲什麼在這兒?你爲什麼不回你自己的國家?”我的祖父說,“啊,那是因爲我們纔是債權人。你們來到我的國家,你們拿走了我所有的黃金和鑽石,你們阻止了我們產業的發展,所以我們現在來收回了。我們來到這裏,是因爲你曾經去到那裏(我的國家)。”統計數據也支持這種說法。
如今當我在倫敦漫步,看到其中的古蹟、漂亮的塔樓和博物館,我覺得其中應該有一間房屬於我,因爲它們是用我或者我祖先的錢建成的。在我的書中,我以註釋內容支持了自己這一說法。書中的註釋部分就有50頁,任何人如果想查看我在哪裏獲得了這些信息,都可以參見原始的研究和文章。
爲什麼你覺得給所有內容附上註釋很重要?
邁耶塔: 世界各地關於移民的探討——實際上那甚至不是探討,根本就是大喊大叫——是有關“講故事”的一場競爭。像美國的特朗普、印度的莫迪、巴西的博索納羅、匈牙利的奧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一樣的民粹主義者大量存在。他們是強者,同時是民粹主義者,而民粹主義者天生擅長講故事。他們懂得如何選擇性地概括,但(也因此)他們講的故事具有欺騙性。能與一個精彩的假故事相抗衡的,只有講得更好的真故事。
更好地講述真實故事的辦法,是要覈實一切事實,而民粹主義者不會這樣做。我認爲,我們在提出觀點時,應確保我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偏見,這真的很重要。人們可能會質疑我們的陳述或立場,但如果你將調查研究呈現出來,他們就無法質疑數據了。

《這是我們的土地:一份移民宣言》
我爲這本書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資料。我爲此到處旅行,去了墨西哥和摩洛哥,還有西班牙和匈牙利。爲了研究移民和邊境問題,至今我已經旅行了很多很多年,同時我知道該如何講述一個故事。我認爲,有三樣東西對這樣一本書非常重要:人類/人性的故事、支持這些故事的統計數據和論點。
我在書中提出的論點是,人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遷徙,而這種遷徙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因此我的書是一本憤怒的書,我反對富裕國家那種驚人的僞善,現在他們說,“不,你不能進入英國。你必須尊重我們的國界。”但當初住在其他國家偷竊和掠奪時,他們從未徵得過任何人的允許。
這是一本憤怒的書,但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這個結局就是,當人們遷徙時,每個人都會受益。比如,當人們來到美國和英國時,兩個國家都從中受益巨大,因爲他們自己沒有生育足夠的孩子。而年輕的移民可能會以他們的能量和活力,爲年老的公民負擔養老金。
我們是怎麼變成了如今這樣,仇恨的語言變得如此普遍?
邁耶塔: 我曾經在(紐約)皇后區一所非常種族主義的公立高中讀書,曾遭受到霸凌和嚴重的種族主義侵害,但後來我離開了那所學校,去上大學,又去了研究生學院,住在紐約,當時每年我都在說,“好吧,這個國家的確正在擺脫它的歷史。”特別是當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總統時,我們感到非常高興,覺得美國已經柳暗花明。
我的祖父曾居住在英國,所以我以前也經常來這裏,我曾經看到過“酷不列顛”(Cool Britannia,90年代媒體用來描述英國文化發達狀態時的用語)文化運動的盛況。倫敦曾經很時髦、文化多元,每個人都想到這裏來。但後來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對人們(特別是所有這些國家中的白人工人階級)來說,是極大的打擊。當時人們充滿了憤怒,而他們也應該憤怒,因爲他們的未來也被竊取了。
在我的記憶中,英國從未像如今這樣兩極分化。英國脫歐最大的驅動因素是對移民的恐懼,這導致了英國曆史上最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舉措。我在書中所呈現的是,對這些國家而言,對移民的恐懼造成的損害遠比移民本身可能帶來的損失大得多。

脫歐支持者在國會廣場慶祝英國正式脫歐 圖片來源:Mary Turner
你提到了那句著名的“我們來到這裏,是因爲你曾經去到那裏(我的國家)”。移民算是一種補償的形式嗎?更寬泛地說,你如何看待這種補償?
邁耶塔: 移民當然應該算作一種補償的形式。我再說一次,數據不會說謊。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是公民身份的不平等。1916年,在後殖民世界中,最富裕的那些國家中的公民比最貧窮國家中的公民富裕33倍。到2000年,最富裕國家中的公民比最貧窮國家中的公民富裕134倍。殖民主義已經被公司殖民主義所取代。
當人們的金錢流出自己的國家時,他們就會做出合乎邏輯的事情,即追隨這些金錢的走向。他們追隨他們的金錢來到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掠奪他們,並在今天繼續掠奪他們。我呼籲移民作爲一種補償的形式,不僅是因爲歷史上的錯誤,也是因爲當前的錯誤——其中最大的錯誤是氣候變化。
美國將過量碳(excess carbon)的三分之一排放到了大氣中,歐洲國家又排放了另外四分之一。這些富裕國家因其排放量擾亂和污染了大氣層,以便發展自己的經濟,並將環境問題留給貧窮國家去買單。
該如何抵抗民族主義的復活?
邁耶塔: 對移民的很多恐懼實際上不是出於經濟,而是出於文化,是一種對“白人會被非白人所取代”的恐懼。不過,那些每天都和移民打交道的人、住在城市裏的人、住在諸如倫敦或紐約或柏林這類地方的人,遠比住在鄉村的人更願意接受移民。大多數投票支持英國退歐的人,幾乎沒有和移民打交道的經驗,因此很容易激起他們對移民的恐懼和仇恨。
但是,到底是誰在煽動這種恐懼和仇恨?是擁有福克斯新聞頻道和多家英國小報(經常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的魯伯特·默多克這類人。打比方說,他們會挑出一起移民男子強姦某個白人女性的孤立罪案,再“舉一反三”地對所有移民做推論,儘管所有證據都表明,絕大多數移民比主要人羣的犯罪率更低。
你很難用枯燥的事實和統計數據去迴應某個衝着你大喊大叫的人,你必須以同樣吸引人的方式去迴應。我回應這些人的方式是去尋找移民本身。這就是爲什麼我有這樣的故事,比如家庭成員在美國-墨西哥邊境的友誼公園(Friendship Park)團聚。這是邊境上唯一允許人們短暫相聚10分鐘的地方。我曾見過一個男人,他已經17年沒有見過他的母親了,他隔着圍欄看他的母親,他不被允許擁抱她或觸摸她,但他可以隔着圍欄看她,告訴她自己有多麼愛她,母親則告訴他自己有多麼想念他,並問他吃得好不好。他把小拇指穿過圍欄,他媽媽也把小拇指穿過圍欄,他們的小拇指觸碰在一起,他們哭了。我也開始哭泣。
媒體在突出這類故事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而這就成了我們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是一名記者,並教授新聞學,我們可以用一種吸引人的方式去講述這些故事。真相站在我們這一邊,這是民粹主義所沒有的東西。這就是爲什麼民粹主義者如此害怕記者和作家。這就是爲什麼記者和作家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槍殺、監禁、謾罵和嘲笑。我們是特朗普、鮑里斯·約翰遜和普京這類人所害怕的人。我們是講真話的人。
在這本書中,你說“詞源(etymology)就是命運”,並探討了不同的移民分類:(長居)移民、尋求庇護者、難民,等等。爲什麼這些不同的名稱很重要?
邁耶塔: 關於從一個國家遷徙到另一個國家的人,有一整套的分類法。你可能是一個經濟移民,你可能是難民,你可能是流放者、遊客,你可能是循環移民(circular migrant,如季節性勞工)。你在邊境(管理局)給出的分類回答簡直生死攸關。一些國家會允許尋求庇護者進入,但不允許經濟移民;另一些國家可能吸收技術移民,但不接收難民。因此,一個需要遷徙至另一國家的人必須弄清楚自己適合的分類。
他們把我們叫做什麼都沒關係,最終我們並不是這些分類。我們不是難民、經濟移民或流放者。我們是人類,行使着我們的天賦人權,在太陽系中這顆美麗的藍綠色寶石上穿行。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