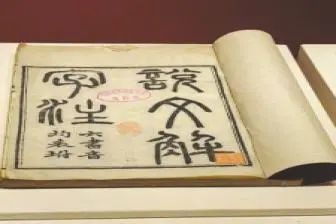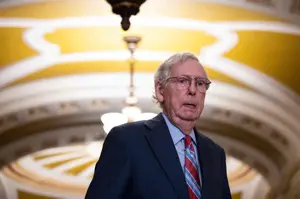作者:尤逢堯
又是一年清明,故鄉的梨花送來了九泉之下母親的淳淳之音,那絲絲如涓的古道,如一道深深思念的河堤,構築着逡巡於我眼簾內多年來的淚水。
母親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而我至今一直認爲她還匍匐於鄉間泥濘的小道與那充滿濃濃煙灰的茅草屋裏,這些年我的思母之情一直停留在這深深的記憶中,從這裏去尋找着我的童年,我的歡樂與往事。
一個詩人說過:童年的記憶是一生的記憶。記憶中的老屋,土牆草舍,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是太祖爺留給子孫們的家產,父親是家中長子,於是就順其自然地繼承了這份奢華的祖上遺產。老屋是我們一家最幸福的記憶,儘管那時候家境貧寒,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但由於有母親健康的身影,爲我們遮風擋雨,給我留下的懷戀是刻骨銘心的。
每年秋收後,我們家就用碾下來的小麥秸稈,給老屋翻新修繕一次,也不是整個屋面都能全部翻新的,僅僅是因爲部分麥草脆爛或鳥兒叼啄後留下洞穴漏雨才補上,孩童時因經歷過多漏雨的折磨,修補房屋倒成了全家最幸福的那一刻;而前牆一直是處於裂痕與傾斜中,於是鄰居房內叔伯們幫忙找來幾根木棍頂上。清文宗咸豐十年的老式農家草屋,那是太祖爺棄文從武參加了太平軍做了師爺,爲保家室安穩而構築了這棟具有黃河故道民風土房。期間經歷了多次朝代更替,加上每年黃泛平原上洪水氾濫的浸淫,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記憶中陽光從低矮的前牆小窗射進小屋時,像一束雄渾的光刀,揮斬小屋的黑暗;唯一能夠透氣的窗戶,就是在屋後啄了個三角形的小洞,小時候很好奇,常常爬到牀上從這個三角小洞向外眺望,屋後一直是濃密的樹林,沒有藍天白雲,但時有鳥語葉香,也會發出嘩嘩啦啦悅耳動聽的響聲。老屋最值錢的是那扇有百年風骨單扇楠木門,門上清晰地留下幾個子彈空,很小時候爺爺就告訴我們,太祖爺是老私塾先生,家裏有點積蓄,辛亥革命期間,軍閥混戰,土匪流氓橫行鄉里,那些彈孔就是當時一幫土匪搶劫我們家留下的。
廢黃河流域夏季常常是暴雨連綿不斷,當暴風雷雨交加時,我們感覺整個屋子都在晃,兄弟姊妹都很小,到處找碗盆等雨水,外面雨停了,而屋內的水卻一直下個不休,老屋吱吱呀呀地搖搖晃晃。天晴了,還有一羣呢喃燕子,飛到屋檐下,築了巢,唧唧喳喳地與我們一起歡唱。老屋門前有顆大槐樹,茂密如碩大無朋的傘,寫滿了我童年的歡歌與笑語,每年夏季我們都會在樹蔭下乘涼,與蟬鳴鳥啼一起聒噪,聽鄰居阿婆給我們講月亮娘娘與玉兔的故事,那時候,我們一直遙想月亮上的玉宮,遙想繽紛多彩的銀河。
老屋情深,那是記憶中最美滿的家,儘管童年充滿着辛酸與惆悵,最讓我難忘的是母親那不知疲倦的身影,那一鍋熱氣騰騰黃亮黃亮的玉米餅,和那一鍋蘿蔔燉肉的油香。黃河故道兩岸飲食習慣是吃煎餅,每家當然都少不了有一盤石磨了,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我家小院中的那一盤厚重的石磨。由於家裏姊妹多,外祖父專門請了北山朋友石匠定做的一個巨大的石磨,一般一個人根本就推不動。我母親人很高大,又很有忍耐力,每天夜裏2點多鐘一個人就起來推磨了,石磨半夜裏常常發出那種吱吱哎哎聲,那就是母親一個人艱難地推磨聲,有時候她半夜實在推不動了就會叫上我,拿半個蘋果或什麼可以吃的東西哄着我,讓我助推一下。我當時是迷迷糊糊的,由於人還矮小,經常會把推磨的棍放到磨漿上了,也是因爲有我稍微助力下,母親就推得更快了。推完我就接着去睡覺,母親便到鍋屋進行烙煎餅,等到天快亮,我們起牀上學時,母親便會把厚厚一疊煎餅疊好了,用紗布包好,父親開始用自行車送我去學校,這樣的日子一直反覆多少年,曾沒有看到過母親感覺到勞累與煩惱。那些年,我母親也只能是30多歲,記憶中的她永遠都是在沉重的石磨上,步履盤纏中走過了她的青春時代。
母親年輕時候歌唱的很好,村裏很多女孩子們都會涌到我們家,跟母親學唱歌,老屋也因此常常煥發着青春的氣息。在母親病重期間我還錄音過,她那清脆悠揚的歌聲時常盤旋在我的耳邊。有一年,我們母親大概32歲左右,她用一年的辛勞養了一頭肥豬,父親帶到集鎮上賣掉了,換回來的錢在還給村裏集體欠款和鄰居家借債時還剩餘點,父親就給母親買了件新衣服,回家後,母親說什麼也不要,讓父親立刻趕回去退掉換成小孩的衣服,父親勸母親留着自己穿,可母親說穿在孩子身上比穿在我自己身上要舒服。在母親再三的要求下,父親只好給我和哥哥分別換了一件紅色背心,清晰記住那時候的快樂,好像人生第一次知道新衣服是漂亮的,孩童時能有一件時尚絢亮的新衣服,別提是多麼高興的事情了,而記憶中,母親永遠都是穿着那一身打着斑斑駁駁補丁的舊衣服,直到她離開我們的那一天。
父親是小學老師,每年學校裏會買一批兒童書,特別是繪本小人畫冊,父親會將書先放在家裏讓我們看,喜愛看書小朋友就會和我交朋友,我很小時候就結交了一大批童年小朋友,那時候農村文化娛樂的生活就是看電影,農村沒有電影院,都是晚上在露天的社場上放映的,鎮上電影也都是在周邊村上循環放映。有一次晚上我去鄰村看電影,一個小朋友悄悄給了我一把落花生,回家後,我把此事告訴了母親。當電影循環到我們村上放映時,母親就讓我把那位小朋友請到家中吃飯,母親說可以多找幾個一起陪伴,小孩子長身體,要多吃飯纔會長得高。後來每逢電影循環到我們村上時,母親都會提前安排晚餐,她一般不去看電影,就會在家裏擀麪條,炒上幾個農家菜,等我們電影結束後,她準時地在家裏擺上一桌豐盛的農家飯菜等着我們,那時候家裏沒有存糧,也沒有錢,主要靠父親每月十幾元的工資,還有我外祖母外祖父的救濟。每個月都會有一場兩場電影來我們村裏放映,母親一直堅持這樣多年,到我家吃飯的同學由開始2-3人,後來升級到10多人了。那些年,母親是35歲左右。
後來上了中學就到外地住校讀書,基本都是週末纔回家,無論什麼時候回家,總是看到母親在翹首以待地等着我,母親早已做好了我最喜歡吃的飯菜。有一年夏季,母親身體真的是出問題了,由於家務沉重及勞作的艱辛,積勞成疾後營養跟不上,醫療落後等原因,在乳腺癌2次手術擴散後,只有躺在牀上了,那一年她剛剛40歲。
母親倒下了,我也一下子長大了,有一天下了晚自習,已是晚上十點多,我一個人走在黑暗的操場上,一時無所適從,甚至怎麼也不能安睡,於是我悄悄地騎上自行車回家。當時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見五指,我憑着感覺飛越穿過長滿蘆葦與荒草的寬寬黃河故道,有時候一陣呼嘯而過的風席捲着一大片蘆葦倒向我,偶爾還有蘆谷鳥哀哀啼啼的鳴叫,我腦子一片空白,拼命地蹬着車,一口氣跑30多裏,到村上時已是夜裏11點多了。一到家,看到臉色蒼白的母親虛弱地躺在牀上,昏暗燈光下,父親請了一位當地半仙寫了個字符,燃燒在碗裏,然後加上半碗涼水讓母親喝下去,他說這樣咒語可以驅出母親身上惡魔,病很快就會好的。
當時母親術後化療不徹底,癌細胞擴散到腦部,母親常常頭痛嚎叫不止,甚至有時候會說糊塗話,偏僻邊遠的農村醫療相當落後,只有聽天由命了。我當時十分想制止此事,但爲了母親能夠早日康復,又別無選擇也只能順其自然。我看到少氣沒力的母親突然從牀上爬起,一咕嚕把一碗燒着紙灰的涼水喝下去了,母親對生命是那般熱愛與如此的渴望,也是源於她的舔犢之愛使命沒有完成。母親看到我回來,從牀上趔趔趄趄站起來,扶着牆走到鍋屋給我燉了一碗荷包蛋,說這麼晚肯定餓壞了,快吃吧。那時候農村看望病人最好的禮物是雞蛋,所以家裏有幾十個親鄰們送來的雞蛋,母親把碗端到我手裏時,我當時是吃不下去的,又無法表達那種情感,只有對着碗,用筷子撥動着,數了下一碗裏竟然有14個荷包蛋,當時,我沒能擡起頭,看着荷包蛋,眼淚簌簌地往下流......
記憶中母親並非是那樣柔弱,甚至是十分強大有力,有一回我哥哥跟幾個小朋友去拾清,被村上最兇悍的看莊稼壯漢盯上了,由於他年齡最小跑得慢,結果被這個壯漢追上爆打了一頓,我母親聽說後,沒有絲毫猶豫,隻身衝到那個壯漢的面前,進行痛斥,幾乎和他動手了。還有一次,母親術後的化療最體弱期間,一個鄰家成年弟兄倆追打尚未成年的哥哥,躺在牀上的母親聽到後,奮不顧身地跑過來,緊緊抓住他們衣服,拖着他們不鬆手,他們無論使多大的勁都沒有掰開母親的手,那時候母親已是臥病不能起牀,自己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也不知道是哪來的那種力量與勇氣.....
這些年始終都不敢回想這一幕,那故道淳樸的母愛猶如雨後蘆葦,有聲有色地輕撫着曲曲折折的河牀,那低矮滄桑的老屋,寫滿了我母親那一代人青春的苦楚與淚光,母親的記憶宛如一首吟唱千秋的故道牧歌,無時不刻地演奏着我噙着淚水的心絃。母親猶如一柱永不謐滅燭光,若隱若明地照亮着我,她那溫存善良、不計得失、不求回報拳拳之愛如同甘甜玉露滋潤着我,她那無畏兇惡、正直善良的愛讓我們學會了堅強,學會明辨是非、學會了知恩圖報。
歲月如棒子米,一粒一粒地流淌在故道的河澗裏,記憶的老屋儘管狹小灰暗,因爲有了一個健康慈愛的母親,我的童年就充滿了無限樂趣與溫馨。母親,您的一生與故道一樣的滄桑,但您亦如那朵朵梨花般斑斕,每至春歸,九曲迴腸的幾百裏黃河故道上漫山遍野的梨花,就是我每年寫給您的最美詩章,清澈緩緩流淌的河水就是我那一行行思念您的熱淚。您常說兒行千里母擔憂,如今,您長眠於長滿祧李菲芳的故道河牀上,終於不用擔憂了,壯觀的樓房吟誦着老屋的記憶,依稀中迴盪着您那清新的笑語與沁人心脾歌聲,您那永不消逝的囑咐,那魂牽夢繞的呼喚始終盤亙在我的心際間,母親,您是我心目中那盞永不熄滅的明燈,照亮着我的每一天、每一刻。
如今,新農村建設與廢黃河生態開發,讓昔日貧瘠的蘇北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幢幢拔地而起樓房,一村村梨花如海的現代農業,每至春歸,鶯歌燕舞,沒有人記得起那個平凡善良誨子不倦的母親,已在這裏靜靜地安詳地沉睡了30多年。當我再次站在這片土地上時,突然發現,母親原來竟是那麼睿智聰慧,儘管她的人生是如此短暫,卻沒有留下她一絲一毫的遺憾,她把所有的美好與記憶都留給了我們,讓我們如此這般深深地懷戀着她,思念着她。每至此,我的腦海裏也總是浮現唐朝詩人李商隱那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正是寫盡了我母親最平凡、最質樸的一生。
(來源:亞太日報)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