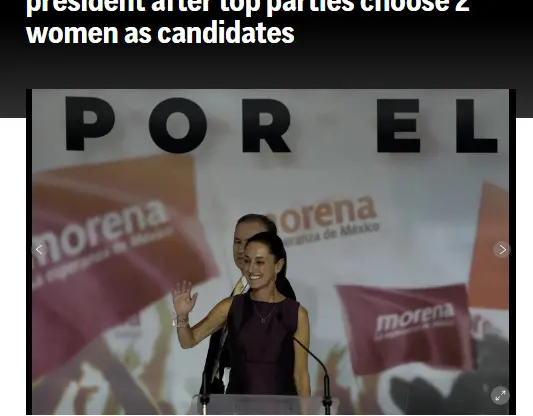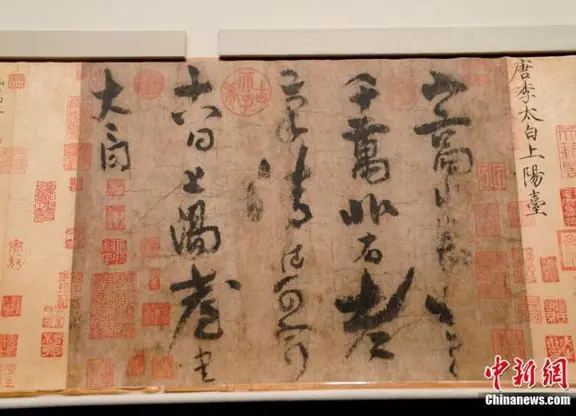2020年似乎註定是要成爲給人類帶來驚喜或驚嚇的年份,在北京時間2月10日頒出的第92屆奧斯卡上,韓國電影《寄生蟲》最終問鼎最佳影片與最佳國際電影,同時導演和編劇之一的奉俊昊也獲得了最佳導演與最佳原創劇本兩項大獎。
這能被稱爲爆冷嗎?或許不能,從頒獎季開始,《寄生蟲》就在收穫的提名與獎項數量一路領跑,只是在一些重要前哨戰沒有獎項收穫,比如美國導演工會獎,奉俊昊壓根就沒入圍,但原因也再簡單不過,他並不是該工會成員。
然而《寄生蟲》畢竟還是一部非英語片,在奧斯卡92年的歷史中,還從未有過非英語片奪得最佳影片大獎的先例,即便是強勢如去年的《羅馬》,或多或少因爲其全片西班牙對白的原因以及Netflix的出身,最終僅僅只拿下了最佳導演、最佳外語片、最佳剪輯三項大獎,最佳影片還是穩妥的被授予了展現種族和解議題的《綠皮書》。

《綠皮書》
而在今年這樣一個被公認爲是奧斯卡大年的年份裏,《寄生蟲》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創造了歷史。情理之中自然是因爲這部電影本身在創作層面具有的優勢,奉俊昊早已爛熟於心的商業類型片技巧讓這部電影能夠在視聽方面獲得最大公約數,與此同時這樣一部聚焦於貧富懸殊與階級對抗主題的作品,即便深刻不足也已經跨過了奧斯卡對電影關注社會議題所劃定的及格線。能夠在去年5月就得到戛納評委的認可,就已經證明這部電影在技術層面已經來到了最高水準的級別。
意料之外則是在於這部電影能夠在北美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超過千萬的票房表現,甚至足以使其能擊敗包括同樣是來自歐洲三大電影節得主的《小丑》、傳奇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的史詩鉅作《愛爾蘭人》、在頒獎季後程脫穎而出的技術流佳作《1917》。

《寄生蟲》
這其中的因素顯然已經不再僅限於電影本身作爲藝術展示的層面,事實上,奧斯卡最大的價值也不在藝術本身。影評人、電影史研究者magasa曾經爲奧斯卡的頒獎品味做出過一個非常簡單卻精確的定義:“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影國家所輸出的一種電影品味典範,這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中影響着人們拍什麼電影,看什麼電影。”
就如同可口可樂與麥當勞一樣,電影同樣是美國作爲世界第一強國最擅長輸出的商品之一,但這種商品的影響更加深遠在於其背後所代表着價值體系,或者說是美國一直引以爲傲的普世價值——宣揚自由民主與多元進步主義,這樣的電影一向容易收穫奧斯卡的青睞。
看看本世紀前20年那些最佳影片吧,《美麗心靈》《國王的演講》《藝術家》這些深受學院派老年白人男性的歷史人物傳記題材無需多言。《指環王:王者再臨》整個三部曲則是當時好萊塢商業大片最高水準的代表,同時天才導演彼得·傑克遜又將完美的正邪對抗融入其中。之後的《拆彈部隊》與《逃離德黑蘭》都是反映美國在中東如何遭遇民主輸出的挫敗,後者更是與好萊塢本身息息相關。進入最近十年,多元主義與種族議題則成爲了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爲奴十二年》與《綠皮書》分別代表瞭如何在當下去講述一個屬於美國傷疤的主題。《月光男孩》與《水形物語》則呼應了新世代崛起後,多元族羣之間應該如何自處的現實問題。

《月光男孩》
但從《月光男孩》到《綠皮書》,這種對於“政治正確”的執迷卻以一種反作用力在瓦解着奧斯卡曾經所驕傲代表着的“美式價值”,因爲這些電影從某種層面來說已經很難在真正的反映現實更遑論影響與輸出價值觀。川普的意外當選成爲了一種標誌,與脫歐問題一併被視爲民主的“失敗”。與此同時,全世界不同地區都在面臨着右翼保守勢力擡頭的現實問題,而貧富差距與階級矛盾恰恰是這背後的重要動因之一。
然而好萊塢有創作者關注到這一點並做出行動了嗎?馬丁·斯科塞斯不惜一切代價拍攝的《愛爾蘭人》講述的還是關於美國當代史與他酷愛的意大利黑幫的故事,昆汀·塔倫蒂諾在《好萊塢往事》中將他對電影作爲一種媒介的運用達到了驢火純青,《婚姻故事》則是典型的紐約文藝中年的愛恨糾葛,《小婦人》則顯而易見的在爲女性主義搖旗吶喊,這些作品都很好,但他們連隔靴搔癢的作用都沒有。所有好萊塢出品的最佳影片提名中,唯一應和了當下現實世界的或許只剩下同樣爆冷拿下了去年金獅獎的《小丑》,但它又太不“正確”了,而且這個人物居然還來自於漫畫。

《小丑》
《寄生蟲》的一句宣傳語爲2020年奧斯卡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不是此時,更待何時?”當下這個時代,是娛樂和藝術摻雜在政治、文化、種族和性別方面掙扎的時代。現在也同樣是階級矛盾成爲全球政治文化衝突核心的年代,在這樣的現實中,傳統“美式普世價值”本身就已經岌岌可危,與其再空洞的高呼自由民主與多元進步的口號,不如勇敢的選擇能夠真切迴應現實的電影,即便它是一部美國人也需要字幕才能看懂的電影。正如《寄生蟲》製片人Kwak Sin-ae所說,“歷史上一個恰當的時刻正在發生”,這確實是對“不是此時,更待何時?”最好的註解。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