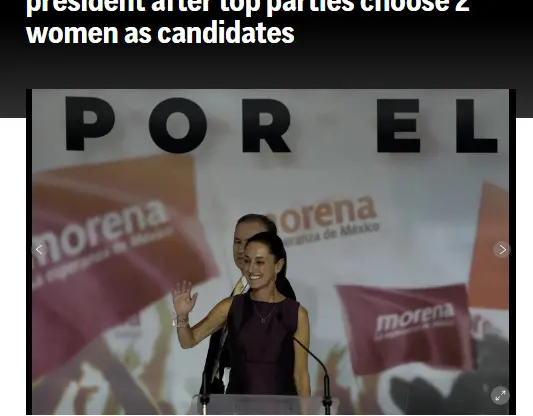1959年,金斯伯格從法學院畢業。當時,女性僅佔美國律師人數的3%,聯邦上訴法院中沒有一名女法官。在收於《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最後的採訪與談話》( Ruth Bader Ginsburg: 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的一篇採訪中,這位已故大法官告訴我們,她當時頂多能成爲一名自食其力的律師。然而,哪怕這一點,都沒法得到保證。《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的內容由七篇這樣的採訪構成,此時出版再適合不過了,十分鼓舞人心。從她那年畢業於哈佛法學院的九名女性之一,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位備受愛戴的美國人,即便反覆重溫她一路走來的過程,金斯伯格的履歷的傳奇程度依舊不減。
金斯伯格於2020年9月去世,享年87歲。《最後的採訪與談話》系列是對已故思想家、作家的一系列的訪談的彙編叢書之一,該叢書採訪的對象包括詹姆斯·鮑德溫、諾拉·埃弗隆和漢娜·阿倫特等。這些採訪的涉及面甚廣,且很直接,它們帶領我們接觸每一位採訪對象,並回溯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金斯伯格在接受本書中的第一篇採訪時,她38歲。那時候的她在接受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職位後,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那是1972年,哥倫比亞大學第一次選擇讓一個女性擔任比講師更高的專職職位。閱讀金斯伯格的言語會讓人產生輕微的眩暈感——我們與作爲一個年輕女性的她相遇,隨後快速地看遍她的一生,直到她去世。不僅如此,她的言語還有種與司法的親密性,這正是傳統的回憶錄所缺乏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顆明星的蛻變。在那第一次採訪中,金斯伯格展現了許多特質,這些特質在後來不僅爲她贏得了尊重與忠誠,還有對於從事她這一行的人士而言不尋常的聲名。當她從哈佛大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並讀成畢業時,她並列班級第一名,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找不到工作。一開始,她告訴記者,她認爲自己一定有問題。“但是,”她說,“當我多次被拒絕後,我意識到,不是我對他們沒用,這背後另有原因。”
1959年,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想要僱用一名女性,哪怕是一個像金斯伯格那樣出色的女性,而她對此事的評論體現出,即使在1972年,她已經同時表現出了溫和的語氣,和麪對霸凌絕對的抵制態度——這種態度成了貫穿她整個職業生涯的印記。當記者問她打算如何做男性團隊中唯一的女人時,她說:“對我來說,唯一的限制條件是時間。我不會爲了來取悅他們而以任何方式減少我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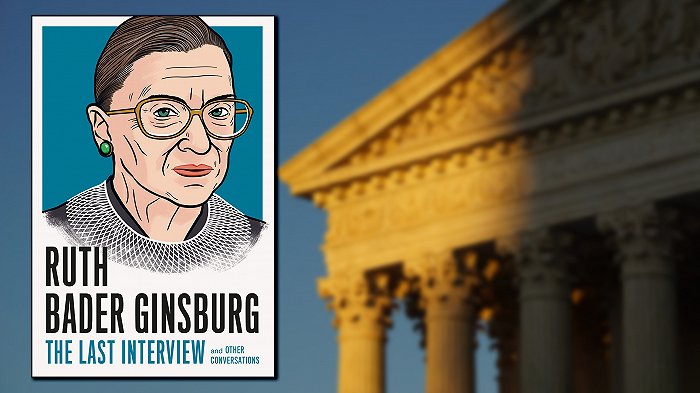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最後的採訪與談話》 背景圖片來源:Ian Hutchinson/Unsplash
正如金斯伯格的對手察覺到的那樣,她的這種語氣具有欺騙性。在2018年由妮娜·託滕貝格(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美國法律事務記者)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進行的一次採訪中,她回顧了自己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時所做的第一件事:她並沒有低下頭顱避免對抗,而是立即與校方對峙,質疑校方爲何解僱了25名女性校工,同時卻保留了所有男性校工。金斯伯格說:“我找到了副校長,並告訴他,學院(這麼做)違反了(校規)第七章。”他回答:“金斯伯格教授,有出色的華爾街律師代表哥倫比亞大學。你想喝杯茶嗎?”
她沒有退縮。她將自己的僱主告上法庭,並獲得了臨時禁制令,以使那些女性免遭解僱。最終,面對公衆要求解僱同等人數的男女職工的壓力,哥倫比亞大學撤銷了其決定,並最終決定不解僱任何人。正如金斯伯格在採訪中乾脆地說道:“面對必須要解僱大約十名男性才能解僱一名女性的問題,他們找到了避免解僱任何人的方法。”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聽金斯伯格講述這場戰鬥和其他許多我從未聽說過的舊日戰鬥帶來的喜悅,如同集會上的呼籲,號召我們在各自的生活中都要更加勇敢。當然,本書還回顧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在哈佛法學院度過的令人恐懼的早年,當時她的丈夫馬蒂被診斷出患有癌症。萬幸的是,他活了下來,但在他接受治療的那一年,金斯伯格不僅要照顧他,還要撫養他們的女兒,攻讀法律學位並做筆記,從而讓馬蒂不至於落下進度。在巨大的壓力下,她帶領整個家庭度過了難關。
這本書的優點在於,採訪的覆蓋面甚廣:從側重於她的司法工作的採訪,到與一羣高中生進行的採訪(這段採訪中的金斯伯格更有趣),再到她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猶太教堂進行的採訪——在這場採訪中,她談到了自己的信仰的重要性。在與學生進行的訪談中,她提到,作爲一個女孩,她曾夢想成爲歌劇歌手,但是,“在我念小學(參與合唱)時,我被分進了‘麻雀組’,而不是‘知更鳥組’,他們讓我對口型。因此,成爲一個偉大的女歌手並不是適合我的道路。”
在另一次採訪中,金斯伯格談到,兒子的學校在遇到需要他們出面的問題時,總是打電話給她,而不是她的丈夫。她直接了當地告訴他們,他們的孩子有兩個家長,校方應該根據需要呼叫他們中的一位。突然之間,校長辦公室不再給她打電話。“我懷疑,”金斯伯格說,“學校不願讓一個男人離開工作崗位,但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讓一位母親離開她的工作崗位。無論如何,我兒子的舉止並沒有很快改變,但是學校幾乎一個學期都沒有打來電話。原因是,在要求一個男人抽出工作時間、來學校之前,他們必須三思。”
在書中,我們還能瞭解到她對綽號“臭名昭著的RBG”的看法,她與已故保守派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的友誼,她對錯誤決定的鎮定自若的態度,以及她如何形成了她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反對意見。與訪談一樣,最微小的人性時刻往往可以揭示最多的東西。在金斯伯格於聖丹斯電影節進行的訪談的結尾處,她多年的朋友託滕貝格講述了一個關於她的故事。託滕伯格說,“當我的前夫去世時,我開始和我現在的醫生丈夫約會,我記得有一天我和金斯伯格大法官一起走下大廳,我說,‘露絲,我已經在約會了。他是波士頓的一名醫生。’我記得她搖晃着她的頭,說道,‘細節。我想要聽所有的細節。’”
本文作者Emma Brockes是《衛報》專欄作家,現居紐約。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