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在波蘭小鎮維爾諾,一個俄國女人在面對鄰居的嘲笑時說:“我的兒子未來會成爲法國大使、作家、榮譽軍團騎士,甚至會成爲將軍,找倫敦最好的裁縫做衣服!”鄰居像聽到癡人說夢一樣大笑,身旁,一個捲髮猶太小男孩沉默不語。那位鄰居不曾想到,往後餘生,男孩都在爲實現母親的願望而努力。這個小男孩就是未來的羅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一位兩次獲得龔古爾獎的傳奇作家。原名羅曼·卡謝夫的加里出生在立陶宛維爾紐斯的猶太人社區,父親做皮貨批發生意,母親經營婦女服飾。一九一五年,由於父親被強制招入俄國軍隊,小加里和母親被流放到俄國中部地區,經受飢餓和嚴寒,當他們五年後回到故鄉時,維爾紐斯已經更名爲維爾諾,被劃分到波蘭境內。

《天根》 [法] 羅曼·加里著王文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加里從小顛沛流離,目睹父母離異、故鄉淪喪,他是一個遊蕩者,對民族或國家的口號充滿警覺。十四歲後,加里來到法國,加入法國國籍,遷徙的生活才告一段落。一九三八年,他應徵入伍,兩年後投奔戴高樂,成爲自由法國部隊的一員。他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獲得十字軍功章,但比他的軍事生涯更顯著的是他的文學生涯。
加里憑藉長篇小說《天根》榮獲龔古爾獎,又用半自傳體小說《童年的許諾》獲得國際聲譽,而他最傳奇的事蹟,要數跟法國文壇開的一個玩笑。一九七五年,一個名叫埃米爾·阿雅爾的作家橫空出世,以小說《來日方長》( La Vie Devant Soi ,又譯《如此人生》)斬獲當年龔古爾獎。但詭異的是,之後長達五年時間裏,文壇都不知道這個埃米爾·阿雅爾究竟是誰。他就如同那位寫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埃萊娜·費蘭特,成爲人們心中的一個謎。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加里開槍自殺,他的友人才公開:埃米爾·阿雅爾就是羅曼·加里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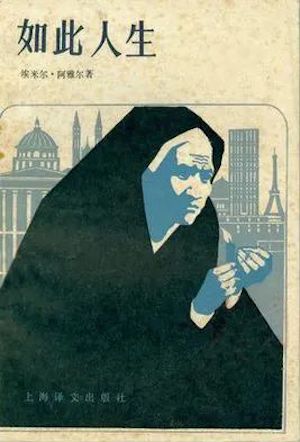
《如此人生》 [法] 埃米爾·阿雅爾著高發明 朱曉敏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
加里出身卑微,但他沒有被生活的屈辱所折服。他的小說塑造了一系列加里式的人物——被拋棄但與生活抗爭的孤兒形象,比如《來日方長》裏的毛毛、《童年的許諾》裏的羅曼、《歐洲教育》裏的揚內茨,他們形象各異,但都有一顆堅韌的心。其頑強鬥爭的一面,在小說《歐洲教育》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歐洲教育》以作者的參戰經驗爲參考,講述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一羣在波蘭維爾諾進行抗德鬥爭的游擊隊員的故事。在這本書中,加里不受固定文體的限制,文字輕盈馳騁,在小說、信件、詩歌裏穿梭;但他的輕盈不是碎碎唸的,當你閱讀的時候,你能感受到文字裏那充沛的力量,那股源於史詩年代的英雄激情和對生命的熱愛。也是在《歐洲教育》中,他書寫信仰,這信仰不在遠方,而在對具體的人的體恤。當歐洲的祥和被戰火燃燒,“行刑隊、奴役、酷刑、強暴——摧毀一切令生活美好的東西”,一批戰士冒着血的代價守護心中的良善。斯大林格勒危機四伏,納粹的子彈隨時讓人殞命,戰士們不是神明,他們害怕死亡,但他們知道,必須有人去戰鬥,爲了人民,也爲了他們所珍惜的價值。
作爲一個戰士,加里珍惜和平,也用文字守護着具體的愛。西蒙娜·薇伊說:“愛是我們貧賤的一種標誌。”在《歐洲教育》裏,愛是守護和平者縱身躍進現實的地獄;而在《童年的許諾》中,愛既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教育,也是兒子哪怕流落他鄉,灰頭土臉,依然把對母親的許諾銘記在心。通過《童年的許諾》,我們能看見加里心中對母親的羈絆。某種程度上,正是他的猶太母親塑造了他的人格,頑強、勇敢、挑戰命運的決心,和那夜深人靜時不爲人知的脆弱。加里揹負着母親的影子生活,即便在功成名就後,他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那段童年與母親共同甘苦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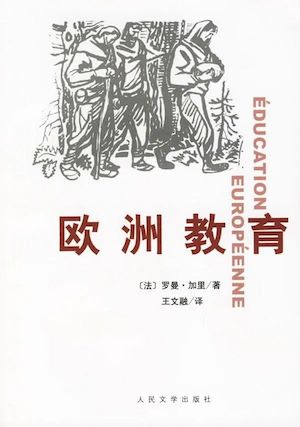
《歐洲教育》 [法]羅曼·加里著 王文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可貴的是,在塑造母親的形象時,加里並未選擇美化。他書寫了母親這一角色的堅強、善良,也毫不避諱她的自私和控制慾。“我媽媽爲了教會我如何驕傲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因此,也鼓勵我讀一本名爲《傑出法國人的一生》的厚重書本。她總會親自高聲地讀給我聽,在念過了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聖女貞德,以及法國民族英雄羅蘭騎士的功績偉業之後,她將書擱在膝頭上,對我投以一種載負着期盼與溫柔的深遠眼光。”這種期待,無形中壓在兒子的肩上,兒子拼盡全力,只爲達到母親的期待;但是,這種疲憊的生活、英雄的聖光,卻也讓他喘不過氣。加里借這段母子關係,探討了兩代人教育中那微妙的感覺。
母親的猶太背景,也讓加里對種族衝突有更深的體會。在俄國、在波蘭,當加里還不是一個戰鬥英雄時,他在別人的冷眼和嘲笑中過活。猶太人在歐洲的歷史,本就是一段錯綜複雜的傷痕史,遷徙的背後,是種族偏見下的驅逐與屠殺。尤其是在“奧斯維辛”後,加里對種族議題有了更強烈的書寫意願。於是在《來日方長》中,他書寫了巴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聚居區裏底層人的生活。在浪漫、繁華的巴黎,有那麼一羣人過着賣淫、乞討乃至偷竊的生活,小說的男主人公毛毛和“賣了一輩子屁股”的妓女羅莎夫人相依爲命。出身妓院,家境貧窮,讓毛毛從小體會到人間的不公,也對人性之惡有更深刻的認識,但惡的普遍,反襯出善的高貴,毛毛在那些被污名化的羣體裏,同樣感受到了善意。羅曼·加里在描寫他們時,流露出惻隱之心。所以小說最後的落腳點是“愛”,哈米勒先生告訴毛毛要相信愛,羅莎夫人也希望毛毛不要放棄,“趁年輕要好好地活”。他們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但他們沒有放棄和苦難生活抗爭的決心。

小說《來日方長》改編的電影《羅莎夫人》(1975)中的毛毛與羅莎夫人
在《來日方長》中,最令人動容的是羅莎夫人,她經歷過集中營,感受過民族間的撕裂,爲了生活忍受着貧困和自以爲是的男人的言語羞辱;但另一方面,她撫養着幾十個“二戰”時妓女們留下的棄嬰,爲這本不必承擔的責任,消耗自己的餘生。唏噓的是,羅莎夫人年老時的心願,只是希望體面地離去。她說:“我的身子已經爲客人服務了三十五年,現在再不能把它交給醫生了,答應我!”她想要安樂死,但最後,她的死亡慘淡孤獨,在偌大的巴黎,如一隻螞蟻被踩死一樣寥人問津,唯獨毛毛守在她屍體邊,用一瓶瓶的香水掩蓋腐臭,他知道羅莎夫人愛美,就竭力爲這個死去的人保持容光,但他也知道,人是敵不過時間的。
從《歐洲教育》《童年的許諾》到《來日方長》,“身份”成爲加里小說的關鍵詞。猶太人、阿拉伯人、土著、移民、妓女、孤兒……“身份”從一出生時就困擾着加里小說中的主角們。《來日方長》中的“我”(也就是小說主人公毛毛),從小失去雙親,他不知道故鄉何處,也不曉得父母去了哪裏,他聽羅莎夫人說,自己叫穆罕穆德,是個地道的穆斯林,可是,“我”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沒有任何出生證件,她怎麼知道“我”是穆斯林呢?當“我”試圖追問羅莎夫人,“我”的母親在哪裏,她爲什麼不來看我,爲什麼我會在巴黎時,羅莎夫人選擇迴避。這些孩子生來被迷霧籠罩,太多空白,讓他們處於失根狀態,對世界充滿了懷疑。
“我”的困境,是很多巴黎孤兒的縮影,加里藉助小說,想要探討爲什麼在同一座城市裏,人與人的童年會那麼不同?爲什麼在付出同等甚至更多勞動的前提下,有些人卻只能活在底層?在法國這個重視平等的國度裏,階層的區隔依然嚴重,基於人種和血緣的偏見,困擾着毛毛這樣的少年。加里移民法國,對此感觸頗深,所以他在讚揚一代代法國人改良社會的熱情時,也呼籲人們放眼當下,不要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

羅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
羅曼·加里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他看到造成羅莎夫人、毛毛等人悲劇的原因,並不純粹是個體智力或努力程度的差距,懸殊的貧富差距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背後,是階層流動性和整體資源分配出現了問題。作爲一個社會名流,加里能數次爲底層發聲,體現出他作爲寫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但或許正是囿於社會身份,讓他的小說在制度批判上不能更進一步,而是轉變爲一種道德敘事,流向一個更抒情的維度。
和加繆一樣,面相憂鬱的加里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的小說裏閃閃發光的人物,在道德上有強大的號召力。加里稱頌的道德並不取決於人物的身份,羅莎夫人是個妓女,但她比很多王公貴族更有利他精神。《童年的許諾》裏的母親在苦難歲月裏的樂觀精神,以及她對孩子無私的愛,更是令人潸然淚下。加里曾說:“人類試圖賦予命運某種形式和含義,神靈們對此心懷忌恨,對我猛烈追擊,弄得我體無完膚,到處是血淋淋的傷口,但是神靈們對我的愛一無所知,他們忘了剪斷這根臍帶。我倖存下來了。母親的意志、勇氣和生命力源源輸入我的體內,繼續哺育着我。”在他筆下,愛成爲黑暗中的花火,於絕望之境傳承希望。這股力量如涓涓溪流,跨越山海與時間。
儘管在大衆面前,加里像個完美的英雄,寫小說,做飛行員,抗擊納粹,但細讀加里的文字,憂鬱、悲憫的色彩就會呈現出來。他不爲強者寫作,而是爲弱者鼓與呼,在他筆下的不是將軍的神話,而是老妓女和小男孩的無聲告白。

羅曼·加里與珍·茜寶(Jean Seberg)
二十世紀是一個製造強人的時代,一個強勢的領袖能夠打贏戰爭,也能讓歐洲成爲煉獄。於是,加里開始反思這種“英雄氣概”,他警惕媒體對強者和犧牲的推崇,他曾說:“煽動英雄主義是對付無力者”,因此,“我最反對強者”。加里用笑的方式寫悲的小說,他筆下的主人公多是弱者,他的文風也不是大氣磅礴、高歌猛進的,而是細膩溫婉,對小人物有深刻的共情。加里是那種用情感制勝的作家,和羅伯·格里耶、西蒙、杜拉斯這些法國新小說派相比,他的小說結構並不酷,敘事也不新潮,甚至透着股十九世紀的樸素,但他善於在樸素的文字中表達動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描繪家庭關係的篇章,一點也沒有矯飾的味道。
晚年,加里和好友加繆一樣,罹患抑鬱症。同樣患有抑鬱症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當紅演員珍·茜寶(Jean Seberg)。因爲被FBI污衊(當時,FBI放出假消息給洛杉磯時報,稱茜寶懷上了黑豹黨頭目休伊特的孩子),她揹負了輿論的巨大壓力,從此情緒低沉,在抑鬱中度過晚年。加繆之死、愛人的抑鬱,讓加里備受打擊,即便在珍·茜寶最受謾罵的時光,他仍力挺妻子。即便後來兩人離婚,加里依然關心着茜寶。曾見過二人的美國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1925-2006)回憶道:“羅曼對於珍的關心,更像是父親對女兒的關心。羅曼告訴我,珍正在接受治療,而她生的病就是曾經同樣折磨過他的抑鬱症。”
許多和加里相處過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好人,在繽紛的社交派對裏,他也總是以樂觀豁達的面貌出現,但回到家中,他會把頭埋在灰暗中,他獨自面對痛苦,在案頭流淚,即便是愛護他的人,也不能解除他的痛苦,那是一種無法完全治癒的創傷,一種突然依賴的恐懼和脆弱,沒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一九八〇年的一天,羅曼·加里在自己的寓所內飲彈自盡。他死的那天,整個法國文壇都陷入哀悼,他們哀悼的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的離去,也是一個憂鬱的人道主義者不爲人知的悲傷。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