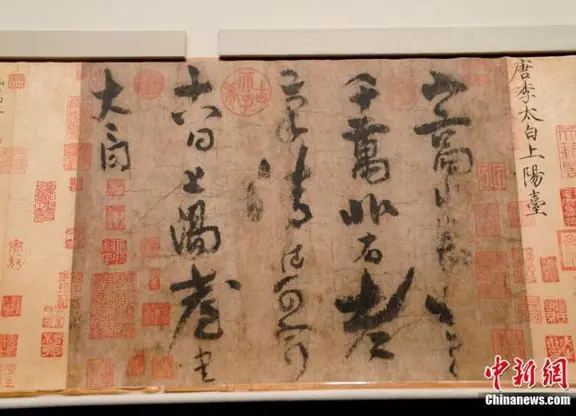很少有人像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那樣對毒品的看法前後發生鉅變。赫胥黎於1894年出生於英國上流社會家庭,目睹了20世紀初的“禁毒戰爭”。當時數年內禁止了兩種極爲流行的麻醉品:可卡因——德國製藥公司Merck曾用其治療嗎啡成癮;海洛因——由德國Bayer製藥公司出於相同治療目的出售。
雙重禁令的發生並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政客和報紙極力渲染“毒品朋友”(癮君子)的負面形象,據稱“他們”因使用可卡因、海洛因和某些安非他命而被“德國的發明所奴役”,這波輿論風潮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湯姆·麥澤(Thom Metzer)的著作《海洛因的誕生和被妖魔化的毒品朋友》。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優生學”言論盛行(既來自阿道夫·希特勒,也來自赫胥黎的哥哥朱利安,後者是臭名昭著的優生主義者),阿道司·赫胥黎想象政府機構使用毒品作爲獨裁控制的邪惡手段。在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的毒品“蘇麻”被髮放給民衆,使他們高興和滿足(“完美地綜合了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優點。”),該書還多次提到墨斯卡靈(迷幻藥,當時赫胥黎並沒有親自嘗試過,但顯然不贊成),使他的角色“琳達”變得愚蠢且易於嘔吐。
赫胥黎後來在《星期六晚郵報》寫道,“明天的專政將剝奪人們的自由,但作爲交換,仍會帶給他們一種真實的、主觀經驗式的幸福,那是一種化學作用……追求幸福是人類的傳統權利之一,不幸的是,實現幸福可能與人類的另一項權利相矛盾,即自由。”在赫胥黎年輕時,成癮性毒品與政治緊密關聯,而在政客和主流媒體看來,對可卡因或海洛因的提倡在很多方面與德國納粹相關。
後來,在1955年的平安夜,即《美麗新世界》出版23年之後,赫胥黎第一次服用了LSD致幻劑。一切都變了,他愛上了它。這啓發他創作了《知覺之門》,並把這種藥物介紹給蒂莫西·利裏,後者極力提倡精神致幻藥物。最終,赫胥黎和利裏的嬉皮政治結盟(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尼克松的總統競選和越南戰爭),很大原因也是他使用此類毒品的美妙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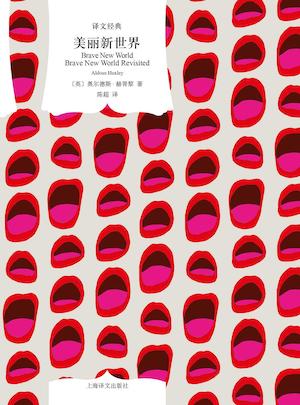
《美麗新世界》 [英]赫胥黎 著陳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6
在赫胥黎的小說《島》中,人們居住在一個烏托邦(而不是《美麗新世界》中的反烏托邦)理想社會,通過服用精神藥物來獲得寧靜和相互理解。在《美麗新世界》中,毒品是政治控制的手段,而在《島》中,毒品是“良藥”。
赫胥黎起初視毒品爲獨裁控制的手段,後來視之爲逃脫政治文化壓制的方式,如何解釋這種轉變?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爲何毒品一度被普遍鄙視,後來又爲部分知識分子和文化權威所推崇?爲何諸如可卡因等毒品曾流行近十年,而後銷聲匿跡,直到幾十年後重又出現?特別是,藥物和毒品如何被用以強調或打破文化邊界?其答案影響到了現代歷史的幾乎各個方面。
藥物和毒品爲觀察我們所處的文化提供了有效的窗口。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流行的藥物和毒品在不斷變化,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可卡因和海洛因、到五六十年代的LSD和巴比妥酸鹽、到八十年代的搖頭丸和(再一次的)可卡因,再到當今諸如阿德拉、莫達非尼和更厲害的類似藥物。人們在特定時期服用的藥物和毒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文化,或者說,人們發明並服用符合當時文化需求的藥品。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藥物和毒品的選擇部分反映了每一代人最大的慾望與缺失。因此,藥品史指向了有待回答的文化問題,無論那是對精神極限的渴求,還是爲了生產力、娛樂、追求標新立異或自由。
需要明確,這項歷史性的調研主要關注精神藥物。它包括LSD、可卡因、海洛因、搖頭丸、巴比妥酸鹽、抗焦慮藥物、鴉片類藥物、阿德拉等,但不包括例如布洛芬等抗炎藥、或撲熱息痛等止痛藥,後兩種藥物並不改變人的心智,因此在進行社會文化分析時作用不大。
在此討論的毒品也觸及了法律(儘管某些毒品是非法的,但不排除它們成爲了某些文化現象的核心)和階級(下層階級所使用的藥品對文化的影響並不亞於上層階級青睞的藥品,儘管後者往往得到了更好的記載並被後世認爲“更具文化影響力”)的界限。最後,此處討論的毒品及藥物類別涉及療愈、醫學和娛樂用途。
要了解我們如何創造和普及毒品以適應我們的文化,請想一想可卡因。可卡因在20世紀初就已出現,又在英國1920年通過的《危險藥品法案》中被宣告非法(以及1922年美國的《麻醉藥品進出口法案》)。據“沉醉毒品的理論家”、《被忽略的嗑藥文化史》( Out of It: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toxication )一書作者斯圖爾特·沃爾頓稱,可卡因在19世紀後期開始流行,很大原因是“它強烈的欣快感”。沃爾頓告訴我,“(可卡因)曾推進對維多利亞時代規範的抵制文化,拋棄了嚴格的禮節,轉向一種‘新藝術運動’時代新興的‘怎樣都好’的社會自由主義(態度),並推動了社會民主政治的興起。”
二戰後,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主義被拋棄,社會自由主義風行,可卡因就在歐美的白人文化中過時了。直到1980年代,可卡因由於新的文化問題再次出現。沃爾頓解釋道,“它在1980年代的迴歸,恰恰是基於相反的社會趨勢:對金融資本和股票交易支配地位的順應,突顯出里根和撒切爾時期企業自利的捲土重來。”
藥品迴應文化問題的另一個例子是,1950年代美國郊區沉迷於巴比妥酸鹽的女性,她們的生活毫無希望、遭受文化壓迫。正如弗裏丹在《女性的奧祕》中所寫,人們期望這類女性“完全獻身於家庭”,並且“只在性被動、男性支配和育兒的母愛中找到滿足感”。沮喪、壓抑而神經質,她們用巴比妥酸鹽麻木自己,以順應尚未被明文反對的規範。在傑奎琳·蘇珊的小說《純真告別》中,三位女主角危險地依賴着興奮劑、鎮靜劑和安眠藥(她們的“玩具”),以順應人生選擇、尤其是社會文化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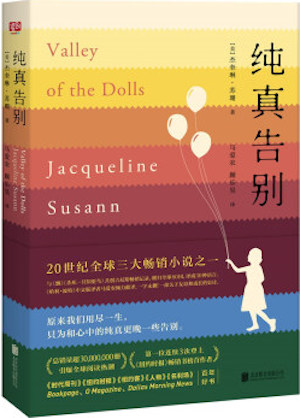
《純真告別》 [美] 傑奎琳·蘇珊 著馬愛農/蒯樂昊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6
但是,處方藥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藥物無法完全解決眼前的文化問題(就像美國郊區的婦女仍然無法擺脫生活中反覆出現的黯然無望),替代藥物(哪怕看上去與眼前的狀況並不相干)往往爲人們提供了潛在的解決辦法。
美國影星朱迪·巴拉班於1950年代在醫生指導下開始服用LSD,當時她才20多歲。她的生活看上去很完美:她是派拉蒙影業富裕而廣受尊敬的總裁的女兒,育有兩女,有一處位於洛杉磯的豪宅,還有一位成功的電影經紀人丈夫(他是馬龍·白蘭度、格利高裏·派克和瑪麗蓮·夢露的經紀人,並與他們結爲朋友)。朱迪·巴拉班是摩納哥王妃、美國女影星格蕾絲·凱莉的密友,並在後者的王室婚禮上成爲伴娘。讓她承認這一點似乎很瘋狂,但在一切光鮮之下——朱迪·巴拉班對自己的生活深感不滿。她同樣養尊處優的朋友也有同感。波莉·貝爾根、琳達·勞森、麥瑞恩·馬歇爾——所有嫁給了著名電影經紀人或導演的女演員,都對生活有着類似的、隱藏的不滿。
由於獲得滿足感的選擇有限,以及服用抗抑鬱藥物的無望生活,巴拉班、貝爾根、勞森和馬歇爾都開始了LSD治療方案。貝爾根在2010年的一篇《名利場》報道中對巴拉班說,“我想成爲我自己,而不是一種人設。”巴拉班則寫道,LSD就像“一支魔杖”,相比抗抑鬱藥物,它更能有效地解決眼前問題。很多和巴拉班一樣受到文化壓抑的同類人羣也有相同感覺,在1950年至1965年間,據報道有4萬人曾接受LSD療法。當時它是合法的,但並不規範,而幾乎所有嘗試過該療法的人都對其功效大加肯定。
LSD不僅受到郊區家庭主婦的青睞,也填補了同性戀或性困惑者內心的缺失。演員加里·格蘭特有數年曾是帥氣的演員蘭道夫·斯科特的室友,同時又與五位不同女性結過婚(婚姻平均長度爲五年,期間他時常和斯科特住在一起),他同樣在LSD療法中獲得釋放。如果當時格蘭特被公認是同性戀,他的電影事業將被毀掉。和那個時代許多郊區婦女一樣,格蘭特將LSD視作急需的“逃生閥”,是昇華痛苦的一種方式。在1959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曾隱晦地說,“我想擺脫自己所有的虛僞。”在精神病醫師指導下的十幾次LSD治療之後,格蘭特承認:“我終於接近幸福了。”

加里·格蘭特和蘭道夫·斯科特在聖莫尼卡的新住所 圖片來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不過有時候,並非是人們尋求藥物和毒品以解決文化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被故意製造出來,以銷售本已存在的藥物或毒品。
例如當今應對多動症最流行的藥物利他能和阿德拉,它們被大量普及,又導致對多動症的診斷顯著增加:在2003至2011年間,美國中小學生被診斷患有多動症的人數上升了43%。這不太像是一種巧合。
“21世紀,對抑鬱症的診斷急劇增加,正如對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多動症的診斷,”美國精神治療師勞倫·斯萊特在《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中寫道,“某些診斷率的上升或下降取決於公衆觀念,但也因爲給病人貼上這些標籤的醫生可能很少考慮該領域規定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標準。”
這也就是說,當今的製藥商催生了一種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認爲不那麼專注且更加沮喪,以便銷售藥物去解決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
激素替代療法也是相似情況,它被用於緩解婦女更年期的不適感,以注射雌激素,有時還有黃體酮,來人爲提高女性荷爾蒙水平。之後該療法又被擴展,包括針對跨性別者和男性雄激素的療法,理論上可以通過激素療法延緩男性的衰老。這種不斷擴張藥物使用量和需求性的慾望,反映了當今藥物所創造(和鼓勵)的文化。
顯然,這種因果關係是雙向的:文化問題可以導致某些藥物流行;但有時流行的藥物又會反過來造就我們的文化。銳舞亞文化(Rave Culture)隨搖頭丸而來,而起初旨在幫助治療認知和注意力障礙的藥物又催生了超高生產力文化……化學藥品與文化之間的共生關係顯而易見。

Thunderdome1996年銳舞狂歡,當年的主題是“不跳舞不成活”(Dance Or Die!) 圖片來源:YouTube/GabberManzion Holland
但是,儘管毒品既可以迴應、又可以創造出全新的文化,卻沒法簡單地解釋,爲什麼一種現象(而不是另一種)產生了。如果銳舞文化是由搖頭丸創造出來的,那麼搖頭丸是否也正在“回答”某一文化問題;或是,搖頭丸只是存在着,而銳舞文化圍繞它興起?我們常常看不清因果關係。
耶魯大學醫學史助理教授亨利·考爾斯表示,“每發明一種會與使用者大腦和心智相互作用的藥物,都會改變研究的對象——藥物使用者。”
以沉迷於巴比妥酸鹽的美國家庭主婦爲例:她們在文化上受到壓制、幾乎沒有自由,因此尋求藥物以迫使自己循規蹈矩。LSD和後來的抗抑鬱藥物是對嚴格的文化規範的“回答”,也是自我治療情緒痛苦的手段。但考爾斯辯稱,同樣可以說,“這些藥物就是爲這種人羣而設計的,最終催生了一種新型家庭主婦或職業女性,她們用藥以維持這種生活方式。”簡而言之,考爾斯說,“只因爲有可能接受藥物治療,才催生了絕望主婦的形象。”
這種解釋將藥物和毒品置於上世紀文化歷史的中心:如果藥物可以創造並強調文化邊界,那麼藥物及其製造者就可以設計整個社會文化的人口形象(例如“絕望的家庭主婦”或“享樂主義的、吸食可卡因的華爾街交易員”)。重要的是,這種文化類別的創造會影響到每一個人,即使不使用該時代中普及藥物的人羣,也會受到身處文化的影響。因果關係並不清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藥物和毒品既可以“回答”文化問題,又可以使文化圍繞它們而生長。
縱觀當下文化,藥物所回答的最大問題也許是“專注”和“生產力”,這是現代“注意力經濟”的結果。對於莫達非尼(用於治療發作性嗜睡病等症狀以保持清醒和增長工作時間)的使用,以及出於類似原因對於其他興奮類藥物(例如阿德拉和利他能)的濫用,正是藥物在試圖回答這些文化問題。
在2008年《自然》雜誌的一項調查中,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曾經使用過認知增強型藥物。據2015年大學生新聞網站The Tab的一項非正式投票顯示,最高的藥物濫用率存在於最知名的學府:牛津大學學生濫用認知增強型藥物的人數比英國其他任何大學都要多。
這些增強認知能力的藥物“在雙重意義上掩蓋了工作中的平庸”,沃爾頓說,“它們刺激用藥者處於一種精神渙散的高度興奮狀態,同時又讓他相信,一定是他在工作中的成功高效才導致了這種亢奮感。”如此一來,現代藥物選擇不僅使人們持續工作並提高生產力,還使他們將更多的情感價值和幸福感寄託於工作中。

舍曲林,抗抑鬱藥物,需長期服用
提高生產力的另一面是,人們對日常生活中更高便利性和享樂性的需求,這種渴望被類似於毒品的體驗(例如ASMR,和其他可以通過互聯網輕鬆獲得的“精神毒品”)所滿足。但是,如果當今的藥物和毒品主要滿足了“注意力經濟”的文化需求(如:專注力、生產力、休閒、便利等),它們也就改變了“成爲自己”的意義。
至關重要的是,正是如今我們用藥的方式反映了“自我”觀念的轉變。所謂的“魔術子彈藥物”(治療針對性問題的一次性或有限療程用藥)已被“維持性藥物”(必須持續服用的藥物)所取代。
“相比舊的模式,這是一種很大的轉變,”考爾斯說:“過去是,‘我是亨利,我有點兒小病。但一顆藥丸可以幫助我做回亨利,然後就不必吃藥了。’而現在是,‘我只有在吃藥後才能做回亨利。’”從1980到2000年,直到現在,使用這類維持性藥物且停藥無望的人口比例只會繼續上漲。
那麼,維持性藥物是否會成爲“後人類”(精神)狀態的第一步?儘管藥物未必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是誰”,但總有某種陰鬱或遲鈍的感覺會重新定義用藥者的基本經歷:“成爲自己”就是“按時服藥”。藥品的未來走向很可能是這種情況的延伸。
在此,讓我們來冷靜地看一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文化與藥物之間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人類曾想要前進的文化方向——無論那是叛逆、屈從,還是完全脫離所有的系統和約束。那麼仔細研究我們今天和未來想要使用的藥品,就可以瞭解未來需要解決的文化問題。當然,這種可能性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較短時間內發生——藥品使人得以完全逃離自我,隨之而來,我們又會看到新的文化問題出現,而解答辦法仍可能是,藥物和毒品。
過去的一個世紀,用藥和毒品的模式令人驚訝地爲我們提供了對文化歷史的準確洞察,從華爾街的銀行家、絕望的家庭主婦,到大學生、文學家,很多人都曾服用藥物或毒品,這些行爲反映出他們的慾望、其所處文化的問題。
藥物和毒品還反映出一種更簡單、持久的老生常談:有時我們想要逃離自己,有時想逃離社會,有時想逃離無聊或貧窮……我們想要“逃離”。在過去,這種渴望是暫時性的——給自己重新充電,找一塊淨土,遠離日常壓力……然而,在最近的時代,用藥或毒品已變爲尋求持久、長期、關於“存在”的逃離——這種渴望非常接近於“無我”(自我消融)。
本文作者Cody Delistraty是一名作家和歷史學家,作品見於《紐約時報》《紐約客》《大西洋》等刊物。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