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孤獨是新聞中的常客,在前新冠時代常常被描述成一種流行病。然而今天,我們正真實地處在一場全球健康危機之中,語境悄然轉變。在一些人看來,社交隔離讓他們得以“獨處”(solitude),如此狀態比“孤獨”(loneliness)要好得多——當然,這麼想的人幾乎都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舒適的小窩。社交媒體上處處可見這兩個詞的對比,大談獨處之趣。薩拉·梅特蘭(Sara Maitland)獨居在蘇格蘭西南部鄉村,在作品《獨處的藝術》中指導人們如何“享受獨處,因爲這和孤獨截然不同”。
獨處與孤獨產生分野是一個現代性的產物,直到19世紀纔出現。幾千年來,“孤獨”(solitude)包含雙重含義。1621年,牛津大學教授羅伯特· 伯頓在《憂鬱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中縱觀了幾百年來的思想,總結道,孤獨是“有所裨益的冥想與沉思”,同時也是叫人憔悴的抑鬱。如此模棱兩可的說法無獨有偶,有的人認爲,即便是對人最爲有利的孤獨也潛藏着可怕的風險。隱居的苦行僧會墮入倦怠(acedia),隱居的學者和詩人常纏鬥在“狂熱的想象”中。魯濱遜·克魯索在島上獨居,雖然每天都在爲生存忙碌,時而能夠得到精神啓迪,但種種苦難與孤獨也排山倒海地涌來。孤獨是永恆的,它的形式遠比樂觀獨居主義者的想象要豐富得多。孤獨也是政治化的,如今比以往更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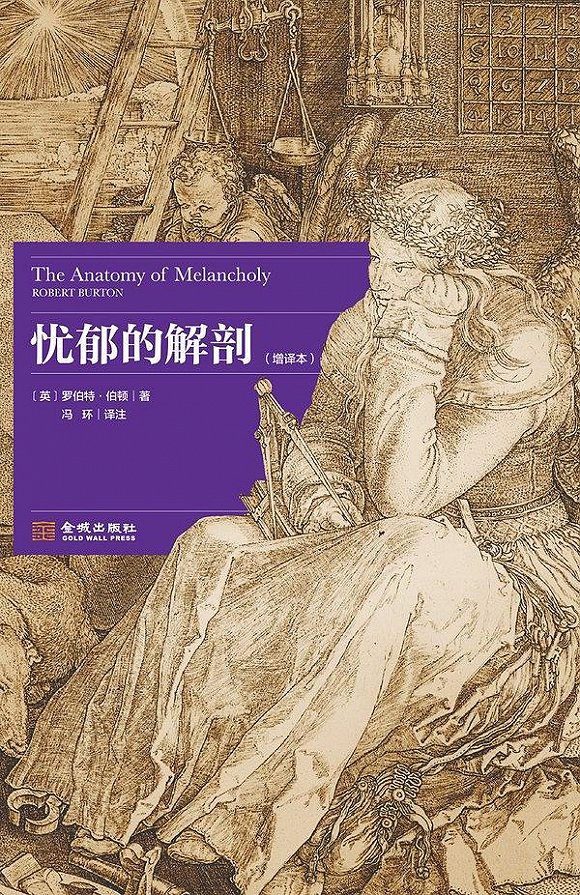
《憂鬱的解剖》 [英]羅伯特·伯頓 著 馮環 譯 金城出版社 2018-8
1951年漢娜·阿倫特對孤立-孤獨之分提出了最爲驚人的一種闡釋。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她認爲,孤立就是“我一個人的共同行動”(alone together with oneself),她追隨蘇格拉底的理論,將其定義爲一種思想中的內在對話(internal dialogue)。然而極權主義的崛起將這種“合二爲一”的孤立狀態取代了,加之以“孤獨”。恐怖陰雲下的人們開始“相互孤立”,他們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類同伴遺棄,進而理性思維讓步於殘忍無情的極權主義邏輯。人們觸發了兩種感受,既丟掉了自我,也丟掉了世界。絕對的孤獨是極權主義的根源,它“摧毀了所有人的共同生活”。
《紐約客》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認爲,阿倫特一語成讖。雖然美國還不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但疫情隔離期間她看到了許多政治帶來的恐懼。按照阿倫特的說法,這些恐怖讓她脫離了自己的思想,陷入一個“悲傷而愚笨”的狀態,被動而孤獨,公共空間與共同行動變得艱險重重。格森不禁發問,“這樣的時代,政治會走向何方?”

警察的監管下,紀念喬治·弗洛伊德的示威羣衆大步經過華盛頓紀念碑 圖片來源: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在格森的文章發表一週後,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殺害,燃起世界各地羣衆心中的怒火,他們紛紛走上街頭。其中大多都是年輕人,許多人都戴着口罩。儘管如此,上街集會依然得冒着生命危險。黑人的生命太重要了,他們無法袖手旁觀。面對這樣的勇氣,英國政府給出了怎樣的回報?只是一次“官方正式調查”罷了——在二十年中已經有七次這樣的調查。這一次主導人是鮑里斯·約翰遜的忠實擁躉,聲稱體制化種族主義是子虛烏有。我們於是必須再度審視這個問題:“這樣的時代,政治會走向何方?”
對阿倫特和格森來說,當人們失去了意識的自我,當恐慌代替了獨立的思考,孤獨就油然而生了。這種解釋太考驗大腦了。英國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經典觀點是,獨處之所以還能忍受,是因爲人們還能擁有關懷。1958年,溫尼科特指出,人之所以能夠忍受孤獨,甚至樂在其中,是因爲在童年早期的時候獲得了父母(通常是母親)的照料。當孩子逐漸成長,這種關愛便內化了,當他們獨處的時候,便能發酵成一種自我陪伴。這種“獨處”是阿倫特所說的“合二爲一”。 溫尼科特在書中寫道,“矛盾的是,獨處的狀態往往意味着有另一個看不見的人在陪伴。”對沒有可靠照料者的人來說,孤獨是無法忍受的。“這樣的人可能長久被囚禁在孤獨中,無法一個人待着。他承受的痛苦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今天,許多人正在遭受孤獨的酷刑。有的人從來沒有享受過照料,享受獨處也無從談起。有的人發現,在強制隔離的社會中,原本能給予照料的系統正在崩潰。慢性病患者、殘疾人、無家可歸的人以及有心理障礙的人、養老院的住戶,無一不面臨着精神危機。研究孤獨的歷史學家弗雷德·庫珀(Fred Cooper)警告說,新冠疫情是許多英國人的“存在性威脅”,讓他們陷入致命的孤立。親朋好友關係被切斷,所有讓他們心有所屬、組成共同體的聯繫都消失了,生命線正在消退,對心理的影響不言而喻。“互助羣(support bubbles)”對某些人也許能起到一些調節作用,但大多數最需要的人並不能接觸到這樣的幫助,甚至會帶來風險。心理健康服務者對此早已不陌生了——自殺率正逐步攀升。
不過,在今天我們還面臨着另外一種孤獨,無一倖免。但當我們向政府求助克服這種孤獨時,卻發現舉目無援。

英國穆塞爾堡的一個老人之家 圖片來源: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和美國的特朗普一樣,在英國,神經大條的鮑里斯·約翰遜、多米尼克·卡明斯和他們的拉拉隊可以說是每一個英國人的“存在性威脅”了,成千上萬的人都沒能倖免,許多人將因此喪失生命,或者以五花八門的方式遭到震盪。違背常理的隔離政策姍姍來遲,隨後又違背科學意見,迅速放寬。感染的住院病人回到療養院,個人防護裝備(PPE)和測試追蹤服務失敗得一塌糊塗。黑人與少數族裔(BAME)羣體易感風險高得不成比例,但他們卻是奮戰在前線的那一撥人。現實令人毛骨悚然,這種恐懼深入骨髓——我們在疾病面前如此脆弱,強權此時多麼無情。
孤獨的危險是真實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照料給其傷害提供了一個緩衝。新冠病毒很可能捲土重來,而我們處在集體性孤獨之中。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爲孤獨鋪平了道路,國家健康服務被資產剝離,福利國家成爲空殼。
新冠疫情之前,孤獨這種“流行病”被當作用來攻擊社會關懷的武器。大衛·文森特(David Vincent)在新書《孤獨史》( A History of Solitude )中寫道,在過去的六十年中,表示自己孤獨的老年人比例並沒有多大的提升。生活的變動(工作、婚姻狀況、地理位置)可能會觸發孤獨感,對年輕人影響尤甚,但即便如此,年輕人孤獨的比例也比英國政府和媒體所報道的要低得多。那麼爲什麼各大頭條都要標榜孤獨是“我們時代的瘟疫”呢?爲的是拆解以公益爲核心價值的服務機構和社會制度,下手對象包括青少年俱樂部、活動中心甚至是公共圖書館,總而言之就是要消解“社會關懷”。英國政府大談孤獨,同時又系統性地摧毀社會聯繫的關鍵來源,其僞善令人歎爲觀止。
現在真正的孤獨危機到來了。在這場危機中,我們抱團取暖。在英國,互助組織和志願行動的指數增長令人目瞪口呆。從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到個人防護裝備,這些社會力量正努力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空缺。“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更是將這種團結延伸到了街頭。除了商業利益所在之處——剛巧這也是英國政府所服務的對象,對陌生人的善意無處不在,企業被施壓,在特殊時期表現一點“同情心”,這可不是天方夜譚嗎。
舍柯芬·薩基(Shokoufeh Sakhi)在八十年代從伊朗流亡到加拿大。她曾在德黑蘭的監獄度過了八年,其中兩年都是獨自禁閉。薩基在博客中寫道,是情感上的聯繫讓她得意存活。現在,她正在多倫多的社交隔離中,反思着大流行病期間,關懷對人們有何種意義:個體與周圍的人們在物理空間上隔離,但也意識到了大家的需要。“我們最後一次集體性地思考自己行動對他人產生影響是什麼時候?我們有清楚的認識嗎?我們是在乎別人的——我們能不能肯定這種古老的感受?在所有這些思考中,全球團結、人民賦權的種子就生根發芽了。”
本文作者Barbara Taylor是惠康基金會研究項目“18-20世紀病態的孤獨”的主要調查人。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