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文學是否已經放棄討論公共生活了?文學和公共生活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日前,2021年“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在上海舉辦。在關於“文學與公共生活”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曾經的礦工陳年喜爲自己的寫作辯護,講述“江湖寫作”的傳統由來已久;在二本院校常年處理行政事務的黃燈講述寫作出自內心,她筆下的鄉村和課堂確實又與更多人有關;我們也看到基層文學刊物主編吐露編輯不易,有些好稿子約不到,又有些稿子不想要都不行。文學關注公共生活當然並不意味着對時代熱點的膚淺追逐,而應當有更自發的、更深層次的呼應。或如詩人張棗爲華萊士·史蒂文斯作序所說的,“世界是一種力量,不僅僅是存在”,世界並不外在於詩歌;生存,這個“堆滿意象的垃圾場”,纔是詩歌的唯一策源地。
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是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共同發起的長期文學研究計劃,以青年性、跨越邊境和拓殖可能性爲目標,每年召集作家、藝術家、編輯、翻譯家、出版人等,在復旦大學-南京師範大學與這兩座城市的文學批評家共同完成主題工作坊對話和研討。此前已經舉行四期,主題分別是文學的冒犯和青年寫作、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以及中國非虛構和非虛構中國。
陳年喜:我的文學出發點是江湖
陳年喜做過16年的爆破工。2015年之前,從南到北,從東向西,中國所有有礦山的地方他都到過。在工作坊發言時,他說自己有很嚴重的職業病,難免會咳嗽,請大家諒解。“我的人生真的很跌宕,我本人真的很江湖,我的寫作也是很江湖的。”陳年喜在《炸裂志》裏記錄了黑暗深處的開礦生活:“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藉此把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身體落滿灰塵”。他自認並不特殊,因爲中國傳統寫作也是很江湖的,“古代的作家詩人也是該騎馬騎馬,該打仗打仗,該流浪江湖的流浪江湖,他們的文學的出發點就是江湖。”
他所理解的公共生活不是熱點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公共生活,“你經歷的那個生活就是你的公共生活,每個人都可以寫出自己在場的、知道的、經歷的生活,組成的是一個時代的景象圖。而這其實是文學非常需要的,不全然是書齋的形態。”陳年喜還對當代詩歌作出點評,認爲如果將當代詩歌放在歷史格局當中,會發現它是“相當弱的”。過去人們從風雅頌的風的部分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愛恨情仇,從杜甫的“三吏三別”裏能夠看到中唐安史之亂的凋敝;回過頭來看當下的詩歌,雖然創作手法更加豐富,但從內容和與時代結合的方面來說還是比較弱的。“一般人對歷史的認識是從詩歌和文學作品開始的,很多人難以接觸到嚴肅系統的史料,而從當代作品回看這個時代,很多東西都看不到。看到的是秋天來了、春天來了這樣一些和生活不是太相關的描寫。詩歌需要時代的氛圍和尺度的開放——像是文學刊物的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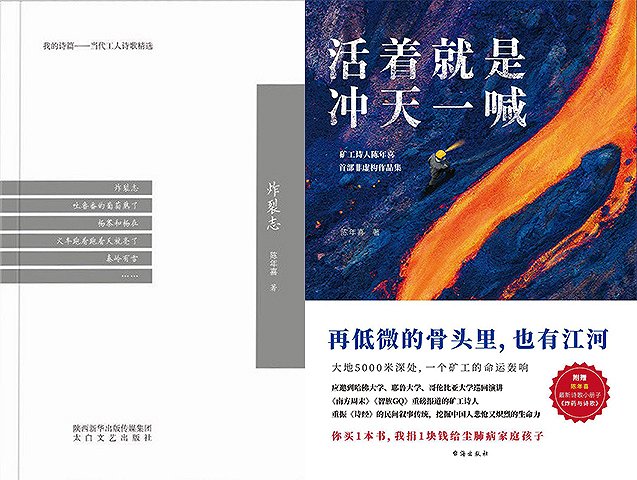
《炸裂志》《活着就是沖天一喊》陳年喜 著
目前陳年喜已經告別礦工身份,從2017年起,他到貴州一家旅遊景區做文案,每天8小時坐班,工作就是負責寫各種軟文以及領導發言。那時候他的工作量不大,兩三天才有一篇,大部分坐班時間都很無聊,就開始寫自己的人生經歷、工友的生活還有家鄉的事情。一方面覺得自己的人生經歷應該有更多人知曉,讓人知道有一羣人在這樣生活;另一方面更多考慮的是收入問題,貴州那家單位開給他的工資是包年5萬塊。他希望這個時代能給非虛構文學一些場地,(作者)能有更多的空間寫作。“非虛構之所以興起,”陳年喜說,“是因爲我們在許多文學作品裏很難讀到真相和世道人心。”
黃燈:個體故事可以爲更多沉默的人賦權
黃燈已經離開了寫作《我的二本學生》時所在的廣東F學院,目前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書。有人評價黃燈的寫作是“剛好找到了一個闡述底層的點”,她覺得這個點並不是自己刻意找到的,生活本就如此,家裏就是有那麼多農村親戚,天天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學生。一次在北京開會,有人跟她說“你真會選IP”,她聽了覺得非常生氣,“這也太小看自動的寫作者了。”
所謂“自動的寫作”,就是完全由自身驅動的寫作,是缺少明確目的性的寫作。以《二本學生》爲例,黃燈教了十四五年書,教過四五千個學生,每次上課都是上百人,黑壓壓一片,這麼多年來也經常被學生當成“垃圾桶”——她沒有主動去做過田野調查,是田野調查找到了她。黃燈說自己不喜歡生硬地介入現實,或是以體驗生活的名義去到特定的場所,“現在動不動就體驗生活,作家要跑到農村扶貧的地方體驗生活,就很怪異,這種創作像被綁架了。”
不管是書寫親人還是記錄學生,這類寫作帶來的麻煩都多過名利的好處。事實上,她離開F學院也與寫作惹出的麻煩有關。黃燈在那所學校待了14年,也做了13年的行政官員,每天被行政事務環繞,最忙的時候一天要開七八場會,連消防事務都要過問一番。在這樣的情形下,她認爲自己寫作中內在的緊張性與反抗性不能通過任何學術或行政評價體系表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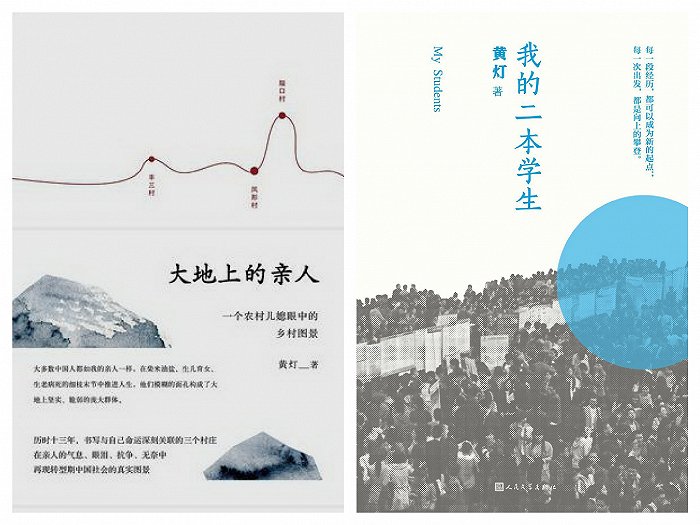
《大地上的親人》與《我的二本學生》 黃燈 著
“我真的是一個學者,”黃燈向與會者強調,她受過的理論訓練讓她可以從現代化、殖民主義、女性主義之類“冠冕堂皇”的話語裏輕易地辨別出同類的氣息,“在那個理論體系裏,如果‘說人話’,大家會認爲你沒水平,你的論文會被拍死掉。”在發現學術這條路差不多被堵死之後,她轉而開始尋找一種在理論語言和論文之外的寫作,要將自己剝得乾乾淨淨,要做個老老實實的人,所有的人物都要有真憑實據。
2016年春節期間引發關注的《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是一篇約稿,在此之後,黃燈用40多天在圖書館的一張桌子上完成了《大地上的親人》,這部書也讓她的寫作進入公共視線,她丈夫的農村家人的生活成爲了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公共故事。黃燈在工作坊的發言中提到,“在《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發表之前,我給我老公寫郵件,因爲這篇文章寫的是他家裏的事情,好歹要經過當事人同意。他一個星期沒有回覆我,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後來我問他,這個事情很多人很忌諱吧,尤其男的,一個女的把家裏事情寫出來怎麼樣。他說,這不是寫我家裏的事情,其實農村很多家庭都是這樣。我們農村很多老人過得很艱難。”個人經驗在很多時候可以跟公共經驗對接,黃燈認爲,至於對接的點在哪裏,取決於個人經驗如何書寫,是寫自己的事情,還是以自己作爲某一類型羣體或者階層的代表。她說,自己所處的“70後”羣體跟中國轉型期完全同步,見證了當代中國的每一次重要改革,“我自己身上就有好多改革措施,”所以,個人的事情也同樣是公共的事情。
是追隨還是淡出?文學與公共生活應距離多遠
陳年喜形容自己的寫作是江湖的,向人們道出這個時代有這樣一羣人在生活;黃燈說《二本學生》是對《大地上的親人》裏“那些農村的孩子讀了書會怎樣的”的迴應,告訴人們農村孩子並不比城裏的笨,雖然他們就算考上大學也不一定是985和211。復旦大學青年副研究員康凌對陳年喜和黃燈的發言做出迴應稱,這二位寫作者的文學公共性,出自他們對追隨熱點的大衆性的抵抗,這樣的文章就像魯迅寫作《狂人日記》不僅僅是出於外在的觸動,而是在長期的自我對話的狀態裏,通過內在的經驗抵抗所謂的“公共關懷”。康凌並不贊成評論家抽着小皮鞭激勵作家書寫“重大題材”的行爲,認爲這是一種文學追隨公共生活的不健康的狀態。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談到了對“附近的人”的田野調查。在距離清華20分鐘車程的高檔小區裏,他認識了一個年輕的保安,保安喜歡讀詩,像是打工詩人許立志的詩,也喜歡寫詩,還參與了皮村文學小組。高檔小區裏豢養着白色孔雀,在小區路上自由行走,他們聊天時白孔雀正在鳴叫。評論家黃德海則對近年來一些同行鼓勵工人寫作的行動表示懷疑,“我想問,鼓勵他們寫作,把他們的情感鍛鍊敏銳了,把他們的文字鍛鍊得更好了,他們接下來怎麼辦?他們感受的痛苦更劇烈了,誰給他提供平臺解決問題?”此外,黃德海認爲,文學對公共生活相對地淡出是對文學的保護,這並不是說文學不應該和公共生活有關,而是說寫作與生活有關必須出自感受最深的一部分,是擴展公共生活的某一點,而不是和公共生活建立起過於友好或同謀的關係。“一個詩人只有在寫作的時候是和寫作有關,如果幹預公共生活,請不要以詩人的身份。文學家有時候在室內太久了,根本不知道公共生活的複雜性。” 他補充說。
可能是出於對公衆評價文學標準的質疑,作家路內在現場朗誦了一段未發表的小說,主要內容是某作家在豆瓣上遭遇一個女性大V差評,由於大V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又引來衆多粉絲差評,他的新書評分瞬間跌破6分,作家開始對惡評進行逐條反擊,形成網絡混戰。作家對這位大V的惡評也十分有趣,形容她是“一手端着紐約客的香檳,一手捧着2萬V的盒飯”。
與對外部生活充滿疑慮的態度不同,一些評論者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評論家方巖在談論文學與公共性的時候感到羞愧無比,因爲這樣談論的時候“是缺什麼才談什麼”,而這樣的公共性的匱乏不是外部環境造成的,而是自己造成的。他認爲,從80年代末到現在,文學批評界對自己一共進行了三次手術——第一次是純文學概念,第二是人文精神大討論,第三是學院化,“這三個手術基本上已經成爲當代文學的三塊遮羞布,是三次自我閹割與自我限制,我們把自己逼到一個角落裏,身上所有複雜的、豐富的東西全部格式化了。我們如果不反省作爲評論者和研究者加在自己身上的種種枷鎖和限制,談文學公共性怎麼都是死路一條。”該場論壇的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項靜表示了對“三次閹割”的異議,她認爲,西方的文學也沒有做三次閹割,但他們也跟我們差不多,處於一種對沒有足夠參與公共事件的自我貶抑中。
巴金故居的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也贊同冒犯的文學,但讓他不滿意的是,現在冒犯的小說越來越少了,好像小說家的美學原則過濾掉了公共性,公共社會中最重要的事件在文學作品裏的呈現,成爲了最隱祕的部分或最簡單的背景。“2020年全球疫情是全世界的大事,是人類歷史的大事,到現在爲止,我們只能讚揚醫生護士嗎?”周立民的反思針對的是當下文學生態,認爲這是一種被馴養的文學,一方面文學生態受到資本的控制,資本雖然不會冒犯公共性,但會製造虛假的生活以擴大和增值,這樣的文學生產首先以盈利爲目的,“餘華《文城》的試讀本,一上來就有那麼多評論,這是沒有資本的普通作家能夠做到的嗎?”另一方面,評獎機制也增強了創作的統一性,“你看到的評委永遠是那些人,一個作家永遠在得各種文學獎,就知道文學不需要個性,也不要側重點,只需要附和獎項的尺度。” 就連曾經野蠻生長的網絡文學也面臨着收編與規訓,周立民點評道,這會讓越來越多趣味趨同的、沒有個性的文學出現,“現在網絡文學作家都可以評職稱了,不是說網絡作家不優秀,而是說,職稱原來規範的對象是誰呢?過去可以野蠻生長的蕪雜之地也逐漸消失了。”
是觀察還是影響:專業文學如何面對基層文學?
周立民發現,自己所在的巴金故居正在成爲熱門的打卡點。據統計,巴金故居在2019年共有37萬人次前來參觀,很多拍照留念的人並沒有看過巴金,也不在乎巴金寫了什麼。除了巴金故居副館長的身份,周立民也主編內部刊物《楊樹浦文藝》——這本刊物被金理稱爲“基層文學刊物”,目前已經出了70期,由楊浦區作協主辦。周立民向與會者強調,很多讀者不會像我們接受過文學教育的人這樣理解文學,他們覺得有詞語的感覺就是文學,所以更需要理解這些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或者說基層文學人士。
《楊樹浦文藝》只能辦到50%的水平,周立民說,因爲這是一份區級作協刊物,他想要跟作家約稿,作家不肯把最好的小說給他,他還要說服人家這是內印刊物,才印2000份,還都全是送的。另一方面,他還要經常與一些不想發的稿子作鬥爭,有的投稿人甚至堵到了認識的文學教授,“人家跟我說你趕緊給他發了,你的刊物又不是什麼像樣的刊物。”楊浦區作協有150個成員,這兩年的問題是招不到年輕的會員,而有的會員老先生已經出了幾十本書。上海作協也有類似的情況,“大概十幾年前他們做過一個統計,裏面的中青年佔到20%以下。”
基層文學與專業文學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基層文學難道僅僅是被觀察的甚至獵奇的對象嗎?周立民試圖溝通兩類文學的關聯:文學本質上就是自我發泄和自娛自樂,有的人寫作有幾百萬字,對他個人也是有價值的;從社會性方面來說,基層文學作者也是經典文學的忠實讀者,對文學的熱愛遠遠超乎想象——用他的話說,“評不上區作協會員也會着急。”此外,基層文學作者對文學的看法可能會影響公衆,因此文學專業人士需要認識到這些並不在自己世界裏的人,如何改變他們的文學趣味會成爲影響公衆文學趣味的關鍵一環。

《楊樹浦文藝》
嚴飛也分享了自己生活中所見的文學愛好者。他認爲社會學家做田野調查,需要呈現出這些受訪者的個性與生命力,餘華《文城》裏描寫人物的段落同樣可以用來想象保安和保潔。兩年前,一位裝窗戶工人到嚴飛家幹活,他的兒子當時讀高三,處於迷茫期,工人請嚴飛加了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兩句。高考落榜後,少年來到北京,和父親一樣做上了裝窗戶的活計。他告訴嚴飛自己喜歡讀書,尤其是加繆的《異鄉人》(即《局外人》),因爲覺得自己就是北京的“異鄉人”。
作家郭爽也提到,自己的表弟在貴州偏遠縣鎮做公務員,她去實地探訪才發現,表弟在房間牆角擺了一個長條板凳,上面放了很多書。她此前從沒想過,工科出身、在縣鎮做公務員的表弟會這麼喜歡閱讀。 表弟還安排一些小青年帶她騎摩托車出去玩,那些小青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或是更低,一般靠打散工過活,他們將郭爽看成了不起的“文化人”,跟她交流心得。他們問,“姐,你有沒有看過《大象席地而坐》?”郭爽說沒看過,對方說,“我看了三遍,覺得很牛。”面對這些青年,郭爽想起自己認識的那些互聯網“新貴”所說的話:最厲害的互聯網產品不是在賺錢,而是在爭奪時間,當所有人都被遊戲或短視頻佔據的時候,就沒有人會看書和電影。她只想對這些自信的“新貴”說,“去你的,有些時間不能也不會被奪走的。 ”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