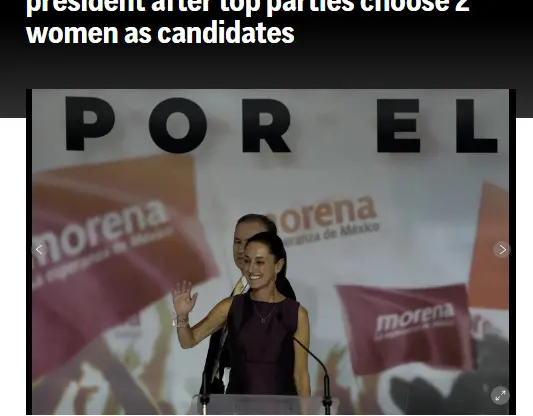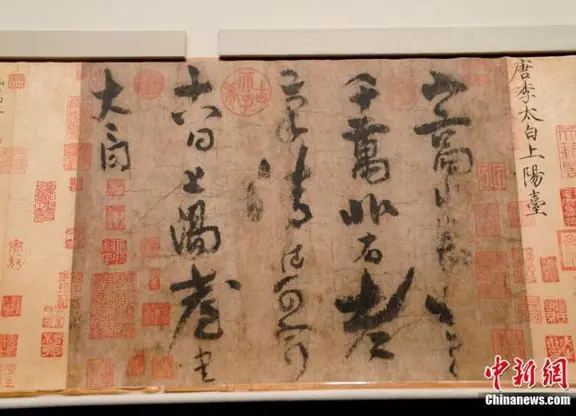去年11月,鋼琴家兼學者薩曼莎·埃格博士在米爾頓宮廷音樂廳舉辦了一場弗洛倫斯·普萊斯、瑪格麗特·邦德斯和維捷斯拉娃·卡普拉洛娃作品的獨奏會。這是英國舞臺上很少聽到的音樂,評論家們“對這些作品的情感吸引力”表示歡迎,而埃格則因其“來源於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精巧表演”而受到讚揚。
然而,沒有人提到埃格的服裝。她對我(指本文作者Leah Broad)說,她穿着一件“受西非風格影響的淡紅色魚尾裙”,光彩照人。緊身胸衣的腰部繫着一條定製的貼花腰帶,在聚光燈下閃閃發光,突顯了面料上的菊石形狀銀色暗花。
對埃格和其他許多獨奏家來說,服裝是表演的重要組成部分。她說:“這給了我表達自己的機會。我考慮到了顏色和情緒,以及服裝會給我和觀衆帶來什麼感覺。”她的裙子來自M.A.DKollection,是專爲巴比肯的演出設計的。“古代和現代……在設計中融合,有力地說明了我的研究和曲目中的主題。我推崇的是黑人文藝復興時期的鋼琴音樂,這個時代反映了文化復興的主題,同時也向過去致敬,但帶有一種以非洲爲中心的轉折。這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我與音樂會服裝的關係!”
薩克斯手傑斯·吉拉姆也有獨特的音樂會風格,以金屬色、醒目的色彩組合和大膽的印花爲主。“我喜歡嘗試給觀衆帶來一種快樂的感覺,”吉拉姆說,“作爲表演者,我的穿着是其中的一部分。”她會選擇讓自己感到舒適和自信的衣服。“我演奏的大多數音樂都是關於表達情感或別人的敘事……要實現這種聯繫,需要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討論服裝在古典音樂中是一種禁忌,對錶演者和評論家都是如此。“大多數音樂家覺得他們不能談論這個問題,”倫敦室內管弦樂團的總監喬斯林·萊特福特說。演奏會的禮服因一系列原因而備受爭議。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認爲,古典音樂家應該被傾聽,而不是被觀看——正如19世紀的評論家E.T.A·霍夫曼所說:“真正的藝術家只爲作品而活……他不會以任何方式展示自己的個性。”在這種理想的表演中,表演者的個性——通過他或她對服裝的選擇來表達——被剔除,服從於“音樂本身”。
因此,那些在着裝選擇上打破常規的音樂人受到了嚴厲地批評——尤其是當他們跨界進入流行音樂領域時,引發了人們對“低能化”的抱怨。但是,圍繞小提琴家奈傑爾·肯尼迪等穿着牛仔褲、留着尖尖髮型的藝術家的爭議,至少有一部分在於,他們提醒我們了現場音樂是一種視覺媒介。我們不只是聽到——我們也看到音樂家表演。
對於女性來說,她們在服裝選擇上的風險要高得多,因爲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性化。雖然肯尼迪的非正式着裝被一些人批評爲“荒唐可笑”,但鋼琴家王羽佳引發的風波卻暴露了一種雙重標準。王羽佳的裙子和她的演奏收到的評論幾乎一樣多——除了幾個例外——評論都集中在她的裙子有多“短和緊”上。
問題不在於評論家們在談論王羽佳的服裝,而是通過性感的視角來看待她穿的衣服。他們首先把她作爲性對象呈現,其次纔是藝術家。在這個世界觀中,沒有空間讓女性的衣服成爲一種藝術和個人選擇。
問題的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時尚不在傳統古典批評家熟悉的範圍之內。“沒錯,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時尚評論家,”諾曼·勒布萊希特寫道,他把王羽佳的裙子描述爲“一件裙襬只在臀部下方一英寸的微型連衣裙”。但這種性感的描述與時尚批評相去甚遠。除了裙子的長度,它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於裙子的信息。面料是什麼?風格?設計師是誰?她的着裝選擇和表演曲目有什麼關係?解決這些問題的語言和技巧可能需要成爲現代評論家所需技能的一部分——如果評論家開始認真對待時尚,經紀人就可以在新聞稿中提供服裝細節,而不必擔心他們所代理的藝術家會因此被貶損。
無法以敏感和尊重的方式談論王羽佳的服裝,這揭示了對女性和她們在古典音樂舞臺上的服裝的長期破壞性假設。我們看到的東西可能會“分散”對音樂的注意力,而不是塑造我們對音樂的體驗,這一觀點源於幾個世紀以來對身體與心靈、身體性與理性的劃分,聲稱古典音樂純粹是大腦活動,身體在這個領域沒有立足之地。這個想法是性別化的。理性和思想在歷史上被編碼爲男性化,而感性和身體是女性化的,結果是女性和她們的身體在古典音樂中被邊緣化。霍夫曼使用“他”作爲他想象中的音樂家的默認代詞,這並非巧合。
對音樂廳裏的女性、她們的衣服和身體提出要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44年,作曲家兼指揮魯思·吉普斯身穿鮮豔的晚禮服出席一場音樂會,遭到了嚴厲的批評,並被樂團管理層告知:“我們不喜歡這種自我宣傳。”吉普斯先是大吃一驚,接着又怒不可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她問道,“居然認爲女人會因爲穿着漂亮的衣服而羞恥?”
這是個好問題。這種敘事需要改變,尤其是因爲無論是對女性服裝的性化還是忽視,都削弱了她們作爲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王羽佳的服裝一直被認爲是一件小事,是一種未經考慮的營銷策略,挑選這些衣服純粹是爲了“展示更多的腿部線條”。爲此,王羽佳被描繪成一個天真、迷茫的音樂家,“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指導來獲得觀點。”因此被更有經驗、更專業的(男性)音樂家們“當作裝飾品”利用。
對王羽佳的主觀能動性的否認,也助長了圍繞女性和亞裔古典音樂家的順從和不愛表達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王羽佳的服裝選擇積極打破了這種偏見。王羽佳是當今最重要的古典表演藝術家之一,但將表演的女性幼稚化是一種古老的策略,目的是削弱她們的地位和個性,遏制和削弱她們潛在的權威。例如,19世紀的女高音珍妮·林德就經常被形容爲“孩子氣”。這些描述往往帶有令人不舒服的性意味,暗示這些女人需要一些年長、強壯的男人來引導她們。
我們需要找到談論女性服裝的方式,尊重她們的藝術選擇,並將其作爲表演的一部分。隨着有關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問題被推到各音樂機構的議程前沿,着裝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例如,倫敦室內管弦樂團最近取消了對演奏者的着裝要求。萊特富特表示,取消對黑領結禮服的嚴重性別化期望,部分是爲了發揚樂團演奏者的個性,併爲那些“身體上表達自我的方式不符合古典音樂刻板印象”的音樂家營造一個包容的空間。但它也創造了一面“觀衆和管絃樂隊之間的鏡子”,向那些“在音樂廳裏感覺不受歡迎的人”伸出橄欖枝。
此外,社交媒體讓古典音樂“更加視覺化”,倫敦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馬克辛·郭說。無論是管絃樂隊還是獨奏家,現在都適應了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自我推廣,從分享音樂會的片段到穿着牛仔褲和套頭衫排練的照片等。也許,這可以成爲一種讓音樂家更容易接近的方式。“我們總需要現代化”,郭指出,而使用社交媒體“增加了一種真正的人文元素”,讓觀衆能夠與他們在舞臺上看到和聽到的音樂人互動。
音樂家不僅僅是他們創造的音樂。我們評估節目表設置中的創意和智力決定——爲什麼服裝不包括在內?19世紀關於古典音樂的觀念——它是什麼,它是由誰創造的,爲誰而創造的,以及關於誰——都已經被顛覆了。關於古典樂的着裝要求的想法也理應如此。
(來源:界面新聞)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